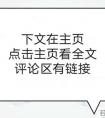(完)未婚夫是小将军,如今他要退婚,理由是只把我当姐姐
我叫沈心慈,当了沈渊八年的准未婚妻,却在他功成名就时被一句“我只把你当姐姐”打发。
全京城都在看我笑话,说我是不值钱的老姑娘。
我反手认将军夫人为义母,开绣坊、建商号,生意做得风生水起。
曾经弃我如敝履的未婚夫红了眼,江南巨富家族找上门认亲。
还有那个总翻我墙头的少年,竟是靖王世子?
01
我十二岁那年,北境战火蔓延,家园倾覆,父母皆殁于乱军之中。是镇北将军沈傲,我父亲的结义兄弟,将我接入府中抚养。初入沈府那日,伯父摸着我的头,对彼时还是个顽皮少年的沈渊说:“渊儿,以后心慈就是你的未婚妻,你要好好待她。”
从此,我成了沈渊的准未婚妻。
八年光阴如水逝去。我跟着伯母学习诗书礼乐,研读账本,手指在冰凉的算盘珠上磨出了薄茧。我学着如何成为一个能配得上未来将军夫人的女子。而沈渊,则跟着伯父驰骋沙场,从小兵做起,一步步历练。
永昌十年,边境大捷,沈渊率铁骑踏破敌国王庭,凯旋还朝。陛下龙心大悦,亲封他为“镇北少将军”,誉满京城,人称“玉面战神”。
他回京那日,万人空巷。我随着伯母站在城楼下迎接,特意换上了他多年前曾说好看的烟霞色罗裙,裙摆绣着细碎的折枝海棠。少年将军银甲白袍,端坐于高头骏马之上,阳光洒在他身上,衬得他眉眼愈发英挺,意气风发,接受着百姓的欢呼。我能听到身边少女们压抑的兴奋低语,她们的目光,如同黏稠的蜜糖,缠绕在他身上。
我的心,也在那片喧嚣中,不受控制地悸动着。喜欢了他整整八年,从懵懂到明晰,我以为,这份漫长而隐秘的期待,终于能等到云开月明。
然而,我终究是天真了。
是夜,月华如练,清冷地铺满了庭院。沈渊站在那棵我亲手栽下的西府海棠下,背对着我。月光勾勒出他挺拔却疏离的背影。
“心慈,”他的声音和他的人一样,带着战场归来的冷硬,一字一句,清晰无比地砸在我心上,“我们自小一起长大,情分深厚。但我思虑良久,始终觉得,我对你,只有姐弟之谊,并无男女之爱。你我的婚约……便就此作罢吧。”
庭院里静得可怕,我能听到自己心脏缓慢下沉的声音。那声音,像是坠入了无底的冰窟。
“你说过,待你建功立业,便……便凤冠霞帔,迎我过门。”我攥紧了袖口,指尖陷入掌心,用尽力气才让声音不至于颤抖得太厉害。
“那是少时不更事的玩笑话,当不得真。”他转过身,目光平静,甚至带着一丝不容置喙的决绝。
“可我当真了……”喉咙像是被什么堵住,酸涩难言。八年的岁月,一个女子最美好的年华,我所有的努力和等待,原来只是一场自以为是的笑话。
他似乎微微一滞,喉结滚动了一下,但眼神依旧冷峻:“我对你生不出恋慕之情,若因婚约勉强成婚,不过是造就一对怨偶,苦果难甜。心慈,你明白吗?”
好一个“苦果难甜”。为了他一句模糊的承诺,我耗了八年。人生,能有几个八年?如今我已二十,在世人眼中,已是明日黄花。全因着这婚约,旁人虽腹诽,却也不敢当面说道。如今,连这层遮羞布,也要被他亲手扯去了。
“沈渊,你是否……有了心仪之人?”我抬起头,强迫自己直视他的眼睛,试图从中找到一丝一毫的犹豫或不忍。
他却避开了我的目光,望向那株在夜风中摇曳的海棠,语气淡漠:“不曾。你很好,母亲常夸你聪慧贤淑,持家有道,是京中闺秀的典范。只是,我的心无法欺瞒自己。我一直,都只把你当做姐姐。”
姐姐……这两个字,像淬了毒的针,细细密密地扎进我四肢百骸。原来我八年的深情,换来的只是“姐姐”二字。
心底最后一丝微弱的火苗,彻底熄灭了。我深吸一口气,压下眼眶中翻涌的湿意,挺直了脊背:“既然如此,强求无益。明日,我便与你一同禀明伯父伯母,解除婚约。”
说完,我不再看他脸上是何神情,决然转身,走向自己的院落。身后,他似乎低唤了一声“心慈姐……”,那声音飘散在风里,我已无心去辨。
回到熟悉的房间,关上门,所有的坚强瞬间土崩瓦解。我瘫坐在门后的石阶上,将脸深深埋入膝间,泪水无声地汹涌而出。委屈、不甘、被全盘否定的难过……种种情绪交织,几乎要将我撕裂。我不怪他变心,我只怪自己,为何要将所有的希望和未来,都寄托在另一个人一句轻飘飘的承诺上。
不知过了多久,夜风带来凉意。我抬起头,泪眼朦胧中,走到院中的石桌旁坐下,望着地上破碎的月影发呆。
忽然,“啪嗒”一声轻响,一颗小石子滚落到我脚边。
我悚然一惊,循声望去,只见院墙头上,不知何时坐了一个人。月光勾勒出他修长的身形,看年纪应与沈渊相仿,却是一身闲适的月白锦袍,而非沈渊的凛冽铠甲。他正怔怔地看着我,脸上带着些许被发现的愕然。
我慌忙用袖子擦去脸上的泪痕,强自镇定,带着浓重的鼻音问道:“你是谁?”
那少年回过神来,眨了眨眼,从墙头一跃而下,动作轻盈利落。他走近几步,隔着石桌与我相对,非但没有惧色,反而饶有兴味地打量着我:“你这姑娘,看着温婉娴静,原来也会哭鼻子?”
他的语气带着几分戏谑,却奇异地并不让人讨厌。我此刻心情低落,也懒得计较,只闷声道:“私闯官邸,你不怕我喊人,把你当贼子抓起来?”
他闻言,非但不怕,反而轻笑出声,露出一口整齐的白牙:“哟,还会吓唬人?”
我心中憋闷,存心要吓他一吓,当即作势要张口呼喊。他果然脸色微变,身形一动,瞬间移至我面前,温热的手掌轻轻捂住了我的嘴。
“嘘——别喊别喊!”
“登徒子!”我又羞又恼,用力掰开他的手,顺势在他脚上狠狠踩了一记。
他吃痛,抱着脚跳开两步,龇牙咧嘴,却还是笑着:“嘶——你这丫头,看着弱不禁风,下手……不,下脚还挺狠。不过……有趣。”
我定睛看他,此人衣着华贵,气质不凡,腰间悬着的羊脂玉佩莹润生光,怎么看都不像是鸡鸣狗盗之徒。倒像是个……走错了门或者心血来潮翻墙玩的富贵闲人。
我叹了口气,重新坐下,疲惫地问道:“你究竟是谁?来将军府做什么?”
少年揉了揉脚踝,也学着我的样子坐在石凳上,歪着头看我,眼神清澈:“现在心情可好些了?”
我微微一怔。经他这一番搅和,胸口的郁结之气,似乎真的散去了些许。哭也哭过了,狼狈也被人看见了,再自怨自艾,也只是徒增笑柄。
我轻轻“嗯”了一声。
他笑了笑,站起身,随意地靠在旁边的海棠树上,姿态慵懒:“我是谁,以后你自会知道。不过我认识你,沈心慈。”
说完,他足尖一点,身形轻飘飘地便跃上了墙头,回头朝我挥了挥手:“桌上那小玩意儿,送你了,算是赔罪。别再哭了,哭花了脸,可就不好看了。”
话音未落,人已消失在墙外夜色中。
我低头,只见石桌上不知何时多了一个小小的木雕。拿起来一看,是一匹栩栩如生、憨态可掬的小马驹,木质温润,雕工精湛。我将小马握在掌心,冰凉的触感却奇异地带来一丝心安。
这木马……似乎有些眼熟,在哪里见过呢?记忆模糊,想不真切。
我将小木马紧紧攥在手里,如同握住了黑暗中一点微弱的星光,转身走进了屋内。
窗外,月已西斜。这一夜,注定漫长。
翌日清晨,我眼下带着淡淡的青影,却将脊背挺得笔直,与沈渊一同去了伯父伯母的主院。
伯父沈傲听闻退婚之事,勃然大怒,一掌拍在黄花梨木桌上,震得茶盏叮当作响:“胡闹!婚姻大事,岂是你说退就退的!心慈等你八年,你如今功成名就,便要做那忘恩负义之徒?”
沈渊直挺挺地跪在地上,面色不变:“父亲,是儿子不孝,辜负了心慈姐姐。但强扭的瓜不甜,儿子无法违心娶一个自己不爱的女子为妻,那才是对她最大的不公。”
我深吸一口气,在伯母担忧的目光中,缓缓跪下,声音清晰而平静:“伯父,伯母,心慈自愿解除婚约。沈渊所言……在理。若无真情,纵有婚约束缚,也不过是同床异梦,徒增怨怼。心慈不愿如此一生,请伯父伯母成全。”
伯母林氏的眼圈瞬间红了,她急忙起身将我扶起,揽入怀中,声音哽咽:“我的心慈儿,你受苦了……是渊儿没福气,是沈家对不住你……”
我靠在伯母温暖的肩头,心中酸涩,却流不出泪来,只是轻声道:“伯母莫要这么说。八年来,您待我如亲生,教我理事,疼我护我,恩同再造。心慈感激不尽。若您不弃,心慈愿认您为义母,日后定当如亲女般孝顺您。”
伯母闻言,先是一愣,随即紧紧抱住我,连声道:“好,好!我的好女儿!从今往后,你就是我林婉清的亲女儿!”
伯父见状,重重叹了口气,目光复杂地看了沈渊一眼,又落在我身上,带着深深的歉疚:“心慈丫头,是伯父教子无方。你放心,即便没了婚约,将军府永远是你的家!至于你这混账小子,”他转向沈渊,“给老子滚去祠堂跪着,没有我的命令,不许起来!”
沈渊沉默地磕了个头,起身径直离去,自始至终,未曾看我一眼。
退婚的消息,像长了翅膀一样,不出半日便传遍了京城。
几日后,我需出门购置些丝线,刚踏入京城最负盛名的“锦绣阁”,便听到了那不甚不小,却足以让我听清的议论。
“瞧,就是她,沈将军家那个养女,被少将军退婚的那个。”
“都二十岁的老姑娘了,还以为能飞上枝头变凤凰呢,结果呢?呵呵。”
“听说在府里就是帮着管管账,像个女管事似的,难怪少将军看不上,男人嘛,谁不喜欢温柔小意的解语花?”
我拿着丝线的手紧了紧,随即又松开。本想置之不理,但那声音越发刺耳。我转过身,目光平静地看向那几位衣着光鲜的贵女,唇角甚至牵起一丝浅浅的弧度:“几位小姐是在议论我吗?”
那几人没料到我会直接发问,一时有些尴尬。为首穿柳绿衣裙的女子强自镇定,嗤笑道:“怎么,做得,还说不得?”
我向前一步,目光扫过她们带着轻蔑的脸,声音不高,却字字清晰:“我沈心慈是否被退婚,年岁几何,似乎与诸位并无干系。倒是诸位,身为名门闺秀,却在此如市井长舌妇般嚼人舌根,议论他人私隐,不知府上长辈可知晓诸位这般‘教养’?若传到令尊或未来婆家耳中,不知会作何感想?”
“你!”几人脸色顿时涨红。
我不给她们反驳的机会,继续道:“至于我是否像女管事,至少我能将将军府庶务打理得井井有条,不知几位小姐除了品茶赏花、议论是非外,可能独立操持一家中馈,看懂账本上的一分一厘?”
她们被我堵得哑口无言,周围已有其他顾客投来异样的目光。那柳绿衣裙的女子气急败坏:“沈心慈,你嚣张什么!不过是个弃妇!”
“弃妇又如何?”我迎上她的目光,毫不退缩,“总好过某些人,连被‘弃’的资格都没有,只能在这里眼红嫉妒,徒逞口舌之快。”
说完,我不再理会她们青白交错的脸色,付了钱,拿着丝线,挺直腰背走出了锦绣阁。身后传来气急败坏的跺脚声和低低的咒骂,我置若罔闻。
走到一条相对僻静的巷口,方才强撑的气势松懈下来,一丝难言的疲惫和委屈涌上心头。我靠在冰冷的墙壁上,微微仰头,不让眼眶里的湿意汇聚。
“骂得漂亮!”一个带着笑意的清朗声音自身侧响起。
我猛地转头,只见那晚翻墙的少年——阿景,正斜倚在对面墙上,抱着臂,笑吟吟地看着我,眼中满是赞赏。
“怎么又是你?”我有些窘迫,刚才那番“泼辣”模样,竟又被他瞧了去。
“路见不平,本想拔刀相助,没想到姑娘自己就把她们杀得片甲不留了。”他走过来,眼神明亮,“被欺负了,就该这样狠狠回击回去。不然,她们只会觉得你好欺负,变本加厉。”
他的话,像一股暖流,悄然渗入我微凉的心田。我低下头,轻声道:“谢谢。”
“心情又不好了?”他歪头看我,语气带着小心翼翼的探询。
我摇了摇头,又点了点头:“有点闷。”
他眼睛一转,打了个响指:“走,带你去个地方,保证你心情豁然开朗!”
“又是翻墙?”我挑眉。
他哈哈一笑:“这次走正门。”
他带着我穿街过巷,最后在城西一处清静却不显偏僻的院落前停下。门楣上挂着朴素的匾额,上书“慈幼院”三字。
院内传来孩童们稚嫩的嬉笑声。一走进去,便有几个年纪不一的孩子围了上来,叽叽喳喳地叫着“阿景哥哥”。
“阿景哥哥,这个漂亮的姐姐是谁呀?”一个扎着双丫髻,脸蛋红扑扑像苹果的小女孩,大胆地拉着我的衣袖,仰头问道。
阿景弯腰将她抱起来,点了点她的小鼻子:“小苹果,这是心慈姐姐。”
另一个胖乎乎像年画娃娃的小男孩挤过来,好奇地捏了捏我的手指:“姐姐的手好软。”
我被这群天真无邪的孩子包围着,看着他们纯净无垢的眼睛,听着他们奶声奶气的话语,心中的阴霾竟真的被驱散了大半。我蹲下身,摸了摸那小胖子的脸,柔声道:“你叫什么名字呀?”
“我叫团子!”小胖子声音洪亮。
阿景在一旁解释道:“这些都是因战乱流离失所,或是父母双亡的孤儿。我建了这慈幼院,请了先生和嬷嬷,教他们识字、学些手艺,也算有个安身立命之所。”
我心中震动,看着他与孩子们嬉戏时那发自内心的笑容,与那晚翻墙的跳脱少年判若两人。他竟有如此悲悯和担当。
“建立这慈幼院,花费不少心血吧?”我轻声问。
阿景将小苹果放下,让她自己去玩,目光望向远处嬉闹的孩子们,眼神变得悠远而温柔:“初衷,是为了完成一个念想。她……是个极好的人,曾说过希望天下孤苦的孩子都能有个归宿。”他顿了顿,收回目光,看向我,笑容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怅惘和坚定,“来日若能重逢,我必倾我所有,凤台麟阁,求娶于她。只望她……莫要拒我于千里之外。”
我看着他眼中那抹真挚甚至带着虔诚的光芒,心中莫名一软,由衷道:“能得公子如此挂念,那位姑娘定是世间难得的佳人。愿公子早日得偿所愿。”
他深深地看着我,笑了笑,未再言语。
夕阳的余晖将我们的影子拉长,交织在慈幼院平整的土地上。看着那些奔跑嬉笑的孩子,一个模糊的念头,如同种子,悄然落入了我的心田。
从慈幼院回来,那个模糊的念头在我心中愈发清晰、坚定。
我不能永远依附将军府。退婚之后,我更需要一份安身立命的本钱,以及属于自己的价值。伯母(如今是义母)虽疼我,但寄人篱下,终究非长久之计。而慈幼院那些孩子渴望又懵懂的眼神,更让我觉得,我或许可以做些什么。
我要开店,经营自己的事业。
我将想法告诉了义母。她听完,沉默良久,拉着我的手,眼中有关切,但更多的是支持:“心慈,你想做什么,就去做。女儿家能有自己的主张和事业,是好事。银钱方面若有不凑手,尽管跟娘说。只是……外面世道复杂,你一个女儿家抛头露面,定要事事小心。”
我心中暖流涌动,伏在她膝上:“谢谢娘。女儿晓得分寸。”
我没有动用义母给的银钱,而是拿出了这些年来自己积攒的所有月例和赏赐,又变卖了几件不大常用的首饰,凑足了初始的本金。我深知,既是自立,便要从头开始。
我并未选择常见的绣庄或成衣铺。京中此类店铺林立,竞争激烈。我在沈府八年,不仅学看账本,对衣物用料、款式配色、乃至各地织造工艺的优劣都了如指掌。我注意到,京中贵眷虽追求奢华,但许多独具匠心的设计和舒适体贴的细节,却少有店铺能兼顾。
我决定开一家名为“云衣坊”的店铺。主营两项:一是承接高端定制,由我亲自根据客人的气质、身形设计独一无二的服饰;二是出售一些我自己设计的、兼具美观与实用,且用料、做工皆属上乘的成衣,目标不仅是贵女,也包括那些讲究品质、却又不想过于张扬的官家小姐和富商女眷。
选址我颇费了一番心思,最终定在了一条连接权贵居住区与繁华商市的安静街道上,既不失格调,又方便客人前来。
接下来是货源。最好的苏杭丝绸、蜀锦、湘绣,都需要稳定的上等货源。我亲自去了西市最大的绸缎庄“华彩阁”。
掌柜见我一个年轻女子,开口便要谈长期合作,采购顶级料子,起初并不十分重视,只让伙计随意拿了几匹中等货色敷衍。
我并不气恼,仔细看了看那几匹料子,缓声道:“掌柜的,这匹杭绸,光泽尚可,但密度不足,易起毛;这匹蜀锦,花纹繁复却失之灵动,金线用量也稍显吝啬,怕是浣洗几次便会失色。‘华彩阁’若只有这等货色,怕是担不起这京中第一绸缎庄的名头。”
那掌柜闻言,脸上敷衍的笑容一收,重新打量了我几眼,神色变得郑重起来:“姑娘好眼力。”他挥手让伙计退下,亲自引我进入内间,拿出了几匹镇店之宝。
我细细抚摸料子,查看织工、晕色,与掌柜侃侃而谈苏绣的“平、光、齐、匀、和、顺、细、密”,蜀锦的“挑花结本”技艺之精妙。掌柜越听越是惊讶,态度也愈发恭敬。
最终,我不仅以合理的价格谈下了长期合作的优惠,更因我的专业和眼光,赢得了掌柜的尊重,他答应,日后有新到的顶级料子,必先送至“云衣坊”供我挑选。
解决了布料,还需技艺精湛的绣娘和裁缝。我深知人才的重要。几经打听,我得知京郊住着一位姓苏的嬷嬷,曾是宫中尚衣局的掌事宫女,手艺超群,因年迈放出宫来。我亲自上门拜访,三次方得一见。
苏嬷嬷起初以年老体衰、不愿再操劳为由拒绝。我并不放弃,第四次上门时,我带去了我亲手绘制的几张服装图样,既有古典韵味,又融入了新颖的剪裁和元素。
苏嬷嬷拿着那几张图样,看了许久,昏花的老眼中渐渐放出光来。她抚摸着我画的缠枝莲纹与流云百福组合的边饰,喃喃道:“这花样……既有古意,又显新巧,搭配得恰到好处。”
我恭敬道:“嬷嬷,技艺需要传承,亦需创新。‘云衣坊’愿为您提供一个施展毕生所学,并能将之发扬光大的地方。工钱待遇,必让您满意。”
苏嬷嬷沉默半晌,终于长长舒了一口气,看着我,点了点头:“丫头,你是个有想法、有魄力的。老婆子我……就再活动活动这把老骨头吧!”
有了苏嬷嬷坐镇,招募其他绣娘和裁缝便顺利了许多。
店铺装修、人员招募紧锣密鼓地进行。这期间,并非一帆风顺。曾有地痞前来滋事,想收“保护费”;也曾有同行听闻风声,故意在办理官府文书时刁难。
然而,那些地痞没过两日便销声匿迹,据说被一位“贵人”派人“敲打”过了。官府的文书也出乎意料地顺利批下。我心中了然,这背后,定是阿景出了力。他虽未明说身份,但能轻易震慑地痞、打通官府关节,绝非常人。我承了他的情,却并未点破,只将这份感激默默记在心里。
阿景时常会“恰好”路过,有时带来慈幼院孩子们送的歪歪扭扭的绣帕,有时只是倚在门口,笑着看我忙碌,偶尔插科打诨,说几句“沈掌柜好大气派”之类的玩笑话。有他在,那些创业初期的疲惫和压力,似乎也减轻了不少。
一个月后,“云衣坊”一切准备就绪,只待吉日开张。我看着布置雅致、货品齐全的店铺,心中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充实与期待。
择了黄道吉日,“云衣坊”在一阵清脆的鞭炮声中正式开业。
我没有大肆铺张,只在门前做了简单的仪式。然而,开业前几日,我精心设计的几款成衣,经由苏嬷嬷和她带领的绣娘裁缝们巧手制成,挂在店内最显眼的位置,便已吸引了过往行人的目光。
一件烟水碧的留仙裙,裙摆采用了渐染工艺,由浅入深,如同水墨晕开,行走间飘逸若仙;一件鹅黄色襦裙,衣襟处别出心裁地用金线盘出细小的缠枝茉莉花纹,低调中透着精致;还有一件绛红色骑射服,剪裁利落,腰身收得极好,既显英气又不失女儿家的秀美。
这些衣服,样式新颖,细节处处见心思,用料更是考究,立刻引起了几位进店观看的官家小姐的兴趣。
“这裙子好奇特,颜色过渡竟如此自然!”
“这茉莉花绣得真活,像是能闻到香味儿似的。”
开业当日,第一位定制客人是位翰林院编修家的刘小姐,她性子娴静,肤色白皙,但身形略显单薄。我为她设计了一身浅藕荷色绣玉兰花的曳地长裙,在肩部和袖口做了特殊处理,用稍挺括的料子衬出轮廓,弥补了她身形过于纤细的不足,玉兰花更显其气质清雅。
刘小姐穿上后,在镜前转了又转,眼中满是惊喜,连声道:“沈姑娘,这衣服……好似专为我而生的一般!”
她满意离去后,不过两日,便又带了两位手帕交前来。口碑,便在这悄无声息中慢慢传开。
真正让“云衣坊”名声大噪的,是一个月后,宫中贤妃娘娘的母亲,一品诰命夫人寿辰。贤妃娘娘为表孝心,欲为母亲定制一套既庄重华贵,又不显过于沉闷的礼服。宫中的尚服局送去的图样,老夫人皆不甚满意。
此事不知怎的传到了那位刘小姐耳中,她向老夫人推荐了“云衣坊”。
我受宠若惊,却也沉着应对。仔细询问了老夫人的年纪、喜好、身形特点及寿宴场合后,我闭门三日,绘出了一套“松鹤延年”褂裙的图样。主体选用沉稳的藏蓝色缂丝,以金线、银线及彩色丝线交错,缂出松枝遒劲、仙鹤翩跹的图案,鹤羽部分采用了罕见的“缀珠绣”,以细小的米珠点缀,光线照射下,流光溢彩,华贵非凡。衣襟和袖口则饰以同色系的祥云纹滚边,庄重中透出仙气。
图样送入府中,老夫人一见便爱不释手,贤妃娘娘也大为赞赏。
接下这单生意,我亲自督工,与苏嬷嬷日夜赶工,每一个细节都力求完美。当成品送达老夫人府上,老夫人试穿后,对着镜中的自己,竟湿了眼眶,连声说这是她这辈子穿过最合心意、最显精神的衣服。
寿宴当日,老夫人身着这套“松鹤延年”礼服亮相,顿时成为全场焦点。所有赴宴的命妇女眷,无不询问这衣服出自何人之手。
“云衣坊”和掌柜沈心慈的名字,一夜之间响彻京城贵妇圈。
订单如雪片般飞来,不仅有各家夫人小姐的定制,甚至连宫中一些低位嫔妃,也悄悄派人出宫,前来下单。
“云衣坊”门庭若市,我不得不又聘请了两位管事和几名伙计,才能勉强应付过来。我每日忙于接待重要客人、敲定设计图样、核对账目,虽忙碌,却感到前所未有的充实与快乐。我看着账本上日益增长的数字,知道自己真正在这京城站稳了脚跟。
这日,我正与一位伯爵府的小姐商讨她及笄礼服的样式,忽感一道复杂的目光落在身上。我抬眼望去,只见沈渊不知何时站在店门外,牵着他的马,正透过橱窗看向店内。
他穿着一身常服,眉宇间少了些许战场杀伐之气,却多了几分沉郁。他看着我从容地与那位伯爵小姐交谈,指点着布料和图样,眼神中有惊讶,有陌生,似乎还有一丝……我看不懂的恍惚。
我与他目光相接,只是微微颔首,便继续与客人交谈,并未因他的到来而有丝毫波动。
他站在门外片刻,最终什么也没说,翻身上马,离开了。
我知道,他看到了一个与将军府后院里那个温顺、等待着的“沈心慈”截然不同的女子。
“云衣坊”的生意愈发红火,我整日忙碌,几乎无暇他顾。这日午后,店里难得清静片刻,我正在内间核对这个月的账目,伙计进来通报,说有一位江南来的老商人,想见见掌柜。
我有些诧异,请了进来。来者是一位年约六旬的老者,衣着体面,精神矍铄,自称姓顾,是江南“云锦记”的东家。他此番进京,本是谈生意,听闻“云衣坊”名声,特来拜访。
我与他寒暄几句,讨论了些江南织造与北方工艺的差异,相谈甚欢。顾老东家说话间,目光却不时落在我脸上,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探究和追忆。
半晌,他忽然放下茶盏,迟疑地开口:“冒昧问一句,沈掌柜……祖籍可是陵水?”
我心中猛地一跳。陵水,那是我早已在记忆中尘封的故乡。自十二岁家破人亡后,我再未对人提起过。
“顾老先生如何得知?”我按捺住心绪,不动声色地问。
顾老东家眼中闪过一丝激动,他凑近了些,压低声音:“像,太像了!沈掌柜的眉眼,尤其是这鼻梁唇形,与老夫一位故去的旧友,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!”
他顿了顿,一字一句道:“那位旧友,姓林,名讳上望下舒,乃是江南织造世家,林家的上一任家主。”
林望舒!
这个名字像一道惊雷,在我脑中炸开。我父亲的名字,正是林望舒!可我家分明是陵水县的普通乡绅,与江南织造世家,有何关联?
“顾老先生,您……是否认错人了?”我声音微颤,“先父确是林望舒,但祖籍陵水,并非什么织造世家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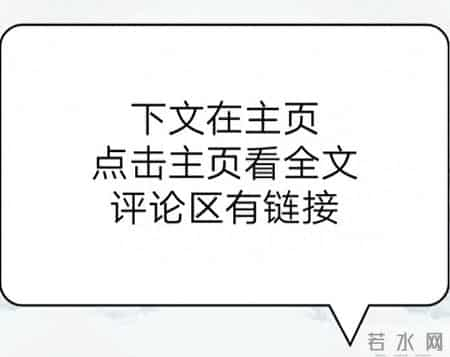
声明:本站所有文章资源内容,如无特殊说明或标注,均为采集网络资源。如若本站内容侵犯了原著者的合法权益,可联系本站删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