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完结)女儿同情她父亲无子,替他纳妾,还将外室之子捧上高台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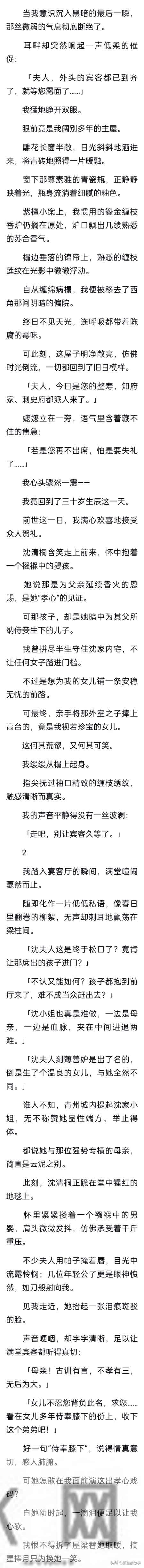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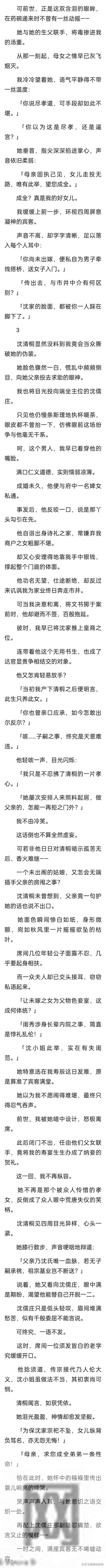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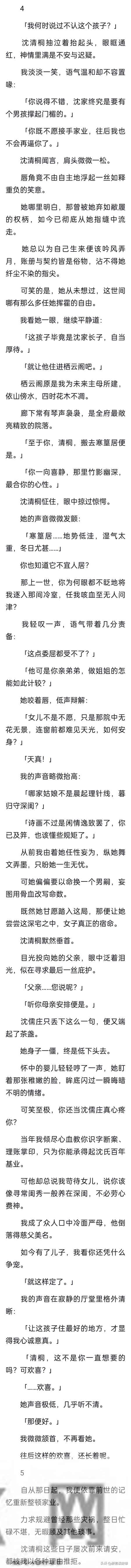
可今日她竟执意候在院外,任凭秋风萧瑟,非要见我一面不可。
我心里清楚她为何而来,便让下人放她进来。
她一进门便委屈地开口,声音带着哽咽:
“母亲,这几日您交给我的那些管事,个个阳奉阴违。”
“是不是您暗中授意他们不听我的?”
真是荒谬至极。
过去十几年里,我对她的纵容与疼爱早已成了她肆意妄为的底气。
如今她背叛在先,却还能如此理直气壮地质问我。
仿佛我所做的一切本就该围绕着她转。
前世的我更是愚蠢,在短暂震怒后便心软原谅。
反倒将过错全归于沈儒庄一人身上。
这一世,我不会再让这对父女轻易脱身。
“没错,我已经把属于你的产业全都收回来了。”
沈清桐闻言,嘴唇微微发颤,眼眶迅速泛红:
“母亲您还在为弟弟的事怪罪女儿吗?”
我冷笑一声,目光平静地看着她:
“你不是一向不屑打理这些俗务?”
“当初我让你接手时,你还闹脾气不愿干。”
“怎么现在没了权柄,反倒急了?”
她脸色一变,急忙道:
“可云姗和她几位兄长都已入股,您突然撤资,让我如何向他们交代?”
赵云姗是襄平侯府的千金,向来与沈清桐交好。
前世我入狱,表面看是家奴作乱、账目不清。
实则背后有襄平侯府暗中操纵。
他们借儿女联姻之名,暗中操控沈清桐名下的铺面。
私设作坊,伪造银票,再通过我沈家的钱路洗白流通。
而沈清桐对此毫不知情,还自以为是在帮朋友。
待我查出真相,她非但不信,反将消息透露给赵云姗。
导致襄平侯府抢先一步毁证灭迹,最后竟将罪名尽数栽赃于我。
重活一世,我岂会再让他们轻易得逞?
“这也是为了你弟弟打算。”
我语气淡然,仿佛在说一件寻常小事:
“从前家中只有你一个孩子,家业自然由你继承。”
“如今不同了,你已是姐姐,凡事当以弟弟为重。”
沈清桐震惊地望着我,声音发抖:
“可可我才是您亲生的女儿啊!”
我轻笑出声,目光却无半点暖意:
“亲生又如何?你弟弟也唤我一声娘。”
“这宅子里的孩子,难道还要分个三六九等不成?”
她之所以敢这般放肆,不过是吃准了我往日的溺爱。
她笃定我会因心疼她而退让,笃定即便有了庶子,我也不会真正舍她而去。
可如今见我态度决绝,她眼中终于浮现出一丝惊慌。
我不想再多费口舌,挥手命她退下。
转身继续翻阅案上那叠厚厚的钱庄账册。
连日挑灯夜战,我终于将账面上的漏洞逐一填补。
虽仍有暗线未清,但短期内尚可稳住局面。
接下来,是时候处理沈儒庄了。
或许是我对庶子的存在表现得太过平静。
又或是见我终日忙于生意无暇理会内宅。
沈儒庄近来愈发猖狂,接连纳了数名侍妾进门。
前世我病卧床榻时,他也是这般得意忘形。
不仅将我珍藏多年的首饰随意赏给新人,还故意带着她们到我房前嬉笑取乐。
此仇,我记了很久。
然而现下毕竟身处世族之家。
若贸然休夫或逐人,难免招来非议,甚至引来觊觎家产之徒趁虚而入。
我虽不惧争斗,却也不想平白树敌。
因此,只能暂且隐忍。
我低头看着手中那封即将送出的密信,眸色渐冷。
待我布局完成,取得足以立足朝堂的凭据,便是清算之时。
在此之前--
先废了他那点得意的资本吧。
6
沈儒庄新娶的妾室里有个出身屠户之家的女子,父亲亡故后被族中叔伯强行卖入沈府。
她曾深夜叩我房门,眼中含泪,只求能做一名粗使婢女,不愿委身侍寝。
我见她虽生于市井,却言谈有度,骨气不折,又知她祖上曾是医户之后,便与她暗中定下“永绝后患”的计策。
那姑娘果真果决,不出数日便在更深人静时动手,一刀斩断了沈儒庄传宗接代的指望。
那一夜惨叫撕裂长空,连巷尾的老狗都狂吠不止,整座宅院仿佛堕入地狱。
事成之后,我依约交付银票,当夜便派人护送她离城远走。
紧接着,我立刻差人前往慈济堂请林大夫前来诊治。
林大夫匆匆赶到,查看伤情后连连摇头,捻须叹道:“性命可保,然根部尽毁,再生无望。”
我佯作悲痛,当即下令遍寻天下名医,广贴告示悬赏百万两以求良方。
消息如风般传开,街头巷尾议论纷纷。
“听说是小妾联手下的毒手。”
“早前沈夫人拦着不让他纳人,如今看来真是明智。”
“男人贪多嚼不烂,惹出祸事也怪不得旁人。”
“为治这病竟肯出百万,沈家这是真急了。”
我自然不会心疼这笔钱——毕竟那物早已埋进土里,再高明的医术也接不回来。
可重金之下,各地郎中纷至沓来,个个自称有秘法奇术。
我一概笑脸相迎,设宴款待,言辞谦恭。
“诸位若能救得我家老爷,便是再造之恩;即便不成,也必有厚酬。”
众医者听罢无不宽心,施展手段时毫无顾忌。
于是沈儒庄先后尝遍艾灸通脉、药汤灌体、炭火炙灼之刑。
更有南疆异士,取活蜈蚣、毒蟾入药,敷于创口,腥臭扑鼻,令其痛哭失声。
还有来自塞外的蒙古医师,执刀剖肌放血,燃草熏体,直把沈儒庄整治得形销骨立,日夜哀嚎。
这些大夫并非不尽心,只是断根复续闻所未闻。
可面对百万巨赏,谁也不愿率先退出,只得继续轮番施治。
整整一个月,沈儒庄在剧痛与恐惧中煎熬,气息日渐微弱。
我看时机已到,便温言遣散众人,每人赠以重金作为谢礼。
至此,沈儒庄再无可救之望,身心俱溃。
像他这般极重颜面之人,如今沦为笑柄,羞愤难当,终日借酒浇愁,动辄拳脚相向于余下妾侍。
我怜她们无辜受累,便逐一备齐妆奁,请媒婆择良人家——许配出门。
如今青州上下皆赞我仁厚宽和,善待下人。
外间传言皆指后院争宠致祸,那些平日荒淫无度的纨绔子弟闻之胆寒,纷纷收敛行径,不敢再轻易纳妾狎妓。
一时间,风气肃然。
毁他一人,清宁一方。
我此举,也算积德深远了。
7
在沈儒庄日渐衰败的日子里,沈清桐为夺回家族产业的事屡次闹腾。
有时装病卧床,有时在园中独自垂泪。
见我始终不为所动,她便闭门不出,整日对着窗外发呆,连饭食也只勉强咽下几口。
我心中冷笑,这些手段早已失去了往日的效力。
曾经我有多宠她,如今就有多厌她!
沈清桐绝食三日之后,终于按捺不住,亲自来我房中请安。
「母亲,下个月是襄平侯夫人的寿辰,家中可有准备贺礼?」
「你觉得送什么合适?」我轻抿一口茶,目光平静地落在她脸上。
沈清桐一心向往侯府,总以为自己能凭才貌博得贵亲青睐,这心思我前世便知,也曾极力劝阻。
襄平侯不受天子重用,常年赋闲在家,府中虽仍维持体面,实则债台高筑。
那侯夫人频频示好,不过是觊觎她手中丰厚嫁妆罢了。
可沈清桐不信,执意认为对方是真心赏识她的风雅与文墨。
前世我苦口婆心相劝,她却充耳不闻。
我终究舍不得她难堪,花重金寻来一幅名家古画作贺礼,她却嫌画风沉闷,不够灵动。
如今我再不愿多费心思。
「侯夫人身份尊崇,寻常物件恐怕难以入眼」沈清桐低着头,指尖绞着衣袖,语气迟疑。
我缓缓放下茶盏:「既然如此,不如你亲手绣一方帕子,再题上几句诗,既显心意,又不失风致。」
沈清桐脸色微变,眉间掠过一丝不悦:
「这般会不会太过寒素?」
「怎会?你常说侯夫人最懂你的才情,既然是知音之人,又怎会在乎礼物轻重?」
她嘴唇微颤,神情尴尬,片刻后又换上一副柔弱模样:「母亲说得是,只是那日宾客众多,皆是名门望族,女儿唯恐礼轻失仪,反让沈家蒙羞。」
呵,从前她总说我太过计较门第,如今倒拿体面来压我了。
「清桐,你要记住,真情不在物重,而在心诚。一朵野花若含深情,胜过千金珍宝;万两黄金若敷衍塞责,也不过是冰冷铜臭。」
这话原是她年少时常对我说的。
我送她明珠美玉,她总推说俗气;而她父亲送一枝梅花、写半首小诗,她却视若至宝。
我若不屑一顾,她便立刻护在身前,言辞激烈。
如今我把她的话原样奉还,她却承受不住了。
沈清桐低头攥着手帕,久久无言,再抬头时眼圈已红,泪光盈盈。
「母亲,侯夫人待我一向慈爱,我只是想好好回报她一番心意」
「回报心意?你父亲卧病多时,汤药无人亲尝,你可曾去守过一晚?」
自妾室尽数遣散后,沈儒庄愈发暴戾,下人们畏之如虎,无人敢近身伺候。
如今沈清桐主动前来,正好让她去尽这份“孝心”。
8
沈清桐向来不善体贴,却最会惹人生气。
头一天去照看她父亲,她竟捧着一叠诗稿进了屋子,说是这些天为激励父亲振作特意写的。
每首皆是苦心雕琢,字句间满是“重燃希望”“再起风云”之意。
谁知沈儒庄刚读了几行,脸色骤变,怒吼一声便扬手甩了她一记耳光。
我正好路过,听闻动静便赶来围观,瞥了眼落在地上的纸页,便明白了几分。
那些“涅槃重生”“再度登峰”的词句,怕是狠狠戳中了沈儒庄的痛处——他如今卧床不起,连起身都艰难,哪受得了这般刺耳的激励?而“莫负年华”一句,更是像针一样扎进他早已溃烂的心底。
他暴跳如雷,骂她是不懂事的蠢货,又接连扇了她几下。
沈清桐站不稳,后退时差点撞到我。
我轻巧地侧身避开,默默退到门外,把这出父女相争的好戏独留给他们。
看了个尽兴,我转身离去,唇角微扬。
从前沈清桐总说我冷心冷情,对丈夫不够体谅,可她自己何曾真正理解过一个被命运击垮的人?
如今亲尝其怒火,才知那所谓“可怜之人”,亦有可恨之处。
夜里,她红着眼来找我,说再也不想去了。
脸上掌痕未消,额边还渗着血丝,说话时声音发颤。
提起沈儒庄时,眼里已没了往日的敬重,只剩委屈与怨愤。
我端坐不动,语气平静:“你父亲虽性情乖戾,终究是你生身之父。孝道二字,岂能因一时委屈便抛下?你若半途而废,外人会如何议论襄平侯夫人之女?”
她身子一僵,泪水滚落,却终究不敢反驳,只能抽泣着离开,重新走向那间令人窒息的病房。
只是从此之后,她的殷勤里多了敷衍,关切中掺了疏离。
沈儒庄毕竟年迈体衰,纵有怒意也难持久;沈清桐年轻灵巧,每每避让得当,偶尔还会反唇相讥。
父女二人日日言语交锋,动辄拍桌怒斥,倒成了府中一段奇景。
谁能想到,这对如今互相憎恶的父女,前世曾联手将我推入绝境?
(未完下文在主页合集,链接在评论)

声明:本站所有文章资源内容,如无特殊说明或标注,均为采集网络资源。如若本站内容侵犯了原著者的合法权益,可联系本站删除。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