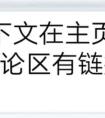(完)被抄家后,皇上赐婚,让我嫁给一个校尉
我曾是大周最耀眼的将门明珠,却在一夜之间家破人亡,被赐婚给一个边关回来的冷硬校尉。
世人笑我明珠暗投,连我心系的三皇子也转身娶了权势郡主。
直到那支淬毒的弩箭射穿他肩膀,这个沉默的男人咳着血问我:“路这么险,你还想和离吗?”
我擦干泪握住他的手:“不想了。萧煜,你在哪里,我就在哪里。”
01
我,江明珠,镇北侯府唯一的嫡女,曾是大周朝最耀眼的将门明珠。
父亲江擎,战功赫赫,执掌北境军权,万民敬仰。三位兄长皆是人中龙凤,军旅俊杰。
我曾以为,我会永远活在父兄的羽翼之下,纵马京城,恣意飞扬,最终风风光光地嫁与我心仪多年的三皇子殿下李瑾。
可一朝风云突变。
八百里加急军报传入京城,非是捷报,竟是构陷!父亲被扣上通敌叛国的弥天大罪,所谓证据“确凿”。
龙颜震怒,下旨彻查。
昔日门庭若市的侯府,顷刻间冷落得能听见落叶的回声。那些谄媚的嘴脸,变得比翻书更快。
最终,侯府男丁,包括我那顶天立地的父亲和三位英武的兄长,被推上法场,血溅刑台。
侯府爵位被夺,家产抄没。
母亲在接二连三的打击下,一病不起,随父兄而去。
偌大的侯府,顷刻间只剩下我这个因是女眷而侥幸活命的孤女。
圣上“开恩”,念及侯府旧功,未将我投入教坊司,而是下旨,将我赐婚给萧煜。
一个刚从边军调入京城不久、毫无根基的六品昭武校尉。
我见过萧煜一次,在父亲还在世时,他来府中述职。沉默,冷硬,像一块边关的风化石,与京城世家子弟的温文尔雅格格不入。我那时满心满眼都是三皇子,何曾正眼瞧过这等人物。
如今,我却要嫁他。我明白,这是皇室对罪臣之女最后的“仁慈”,也是将我这烫手山芋丢出去的最快方式。而萧煜,他不敢抗旨。
婚礼仓促简陋。一顶小轿,悄无声息地从破败的侯府侧门抬出,抬进了萧煜那座只有三进的小院。
新房内,红烛摇曳,却映不出半分喜气。我穿着不合身的嫁衣端坐床沿,盖头下的脸,一片冰冷。
脚步声响起,沉稳有力。盖头被挑起,我抬头,对上萧煜深邃的眼眸。他五官轮廓分明,肤色是边关磨砺出的古铜色,穿着大红喜服,依旧掩不住行伍之气。
“江小姐。”他开口,声音低沉。
“萧校尉。”我回应,同样冷淡。
我深吸一口气,直接摊牌:“这场婚事因何而来,你我心知肚明。我心中旧事未了,嫁你实属无奈。我们约法三章,可好?”
他静静看着我,默许。
“第一,你我虽有夫妻之名,但不行夫妻之实。待我父兄沉冤得雪之日,便是我们和离之时。”
“第二,在此期间,互不干涉,你不得限制我的自由。”
“第三,人前我可与你做戏,人后你我各不相干。”
我一口气说完,紧紧盯着他。
萧煜只是沉默了片刻,然后点了点头,简单吐出一个字:“好。”
他的爽快,让我微微一怔。随即是更深的悲凉。果然,娶我于他亦是拖累。
“既如此,今夜就请萧校尉自便吧。”我指了指角落那张矮榻。
萧煜目光扫过拔步床,又落回我脸上。没有争辩,他转身从柜中取出一床薄被,利落地铺在矮榻上。
红烛燃了半宿。我躺在床上,毫无睡意,听着不远处均匀轻微的呼吸声。
这个男人,像一口深不见底的古井。不过没关系,我告诉自己,江明珠,记住你的目的。这只是蛰伏。李瑾哥哥一定会想办法为我江家洗刷冤屈!到那时,我便能离开。
翌日清晨,我醒来时,矮榻已空,被子叠得如同军营行囊。
丫鬟采薇端水进来,低声道:“小姐,萧校尉他一早就接到兵部命令,前往北疆公干了,说是归期未定。”
走了?我心底莫名一松。走了也好。
走到窗边,推开窗,萧瑟秋景映入眼帘。父兄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。泪水模糊了视线,但我倔强地没有让它流下。
我不能倒下去。我必须活着,等到真相大白、血债血偿的那一天。
萧煜,一个过客而已。我的未来,绝不困于此地。
萧煜这一去,便是数月。秋去冬来,院中残雪未消,更显清冷。采薇尽力打点,但仆从寥寥,沉默寡言,与昔日侯府盛况相比,云泥之别。
往日的“好姐妹”,如今的康宁伯世子夫人柳如烟递帖来访。我本不欲见,终究耐不住死寂,请了她进来。
她云锦华服,环佩叮当,满面春风,与我半旧的素裙形成刺眼对比。
“明珠妹妹,”她亲热拉我手,眼底却藏不住优越与怜悯,“清减了许多。这萧府……到底是简薄,委屈你了。”
我抽回手:“柳姐姐说笑,我能有片瓦遮头,已是隆恩。”
柳如烟掩唇一笑:“妹妹何必妄自菲薄?前几日在安王妃赏花宴上,我瞧见三皇子殿下了。”她刻意顿了顿,“殿下身边伴着瑞敏郡主,两人言笑晏晏,甚是般配呢。”
我的心像被针扎,细密的疼蔓延开。瑞敏郡主,端亲王嫡女,如今京城最炙手可热的贵女。
“是么?”我端茶,借热气掩饰苍白的脸,“殿下之事,非臣妇该议。”
柳如烟见我不接茬,又絮叨许多京中“趣闻”,字字句句提醒我已是局外人。
送走她,胸中郁结难平。三皇子……那些誓言,果真随风散了?
“采薇,备车,去城南‘清茗轩’。”我需要透口气,在那熟悉雅座里,或许能觅得一丝往日的幻影。
清茗轩是我未出阁时常来的茶楼。我戴帷帽,与采薇悄然上楼,走向惯常的“听雨阁”。
推开门,我愣住了。
一人负手立于窗前,身姿挺拔,闻声转身,眉目温润,唇含浅笑——正是三皇子李瑾。
“明珠。”他柔声唤,眼中带着惊喜与关切。
我僵在门口,心跳骤乱。“殿下?您怎会在此?”
“听闻你心情郁结,我放心不下。”他示意采薇关门在外,仔细端详我,“瘦了。在萧家……可好?萧煜可有为难你?”
关切话语如暖流,冲垮心防。鼻尖一酸,我几乎落泪。“他……出征未归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李瑾叹息,声音更柔,“明珠,委屈你了。嫁给那般粗鄙武夫……”
我低头哽咽:“殿下,我父兄的冤屈……”
“我一直在查!”他语气坚定,“你放心,我从未忘记对江侯爷的承诺,也从未忘记你。只是此案牵涉甚广,需从长计议。你耐心等待,我必会还江家清白!”
他的承诺如暗夜灯塔,让我重燃希望。“真的?”
“自然。”李瑾握住我的手,目光灼灼,“明珠,你信我。待你父兄沉冤得雪,你恢复自由身,我……”未尽之言,情意分明。
就在这时,门外传来喧哗,一个沉稳男声隐约道:“……萧大人北疆归来,已至城外驿站,不日将入京叙功……”
萧煜?回来了?这么快?我心中一动。
李瑾显然也听到,他松开手,神色微凝,低声道:“明珠,你先回去。记住,耐心等待,一切有我。”
我五味杂陈,点头,戴帷帽匆匆离去。
回府马车中,思绪纷乱。李瑾的承诺让我心生慰藉,可“萧煜归来”的消息,却像石子投入心湖,扰乱了方才的波澜。
那个沉默冷硬、被我视为过客的男人,似乎并不如我想象的那般……无足轻重。
萧煜归京的消息很快传开。他在北疆一次针对游寇的突袭中身先士卒,不仅剿灭了为祸商路的马贼,还顺藤摸瓜截获了北狄探子试图传递的密信,立下不小的功劳。兵部叙功,他被擢升为从五品游骑将军,正式在京城官场有了一席之地。
他回府那日,天色已近黄昏。我正与采薇在廊下看着仆妇清扫残雪,院门处传来声响。抬头看去,萧煜一身风尘未洗的墨色劲装,大步走入。数月边关风霜,似乎让他原本冷硬的轮廓更深了些,肤色也更黝黑,唯独那双眼睛,在暮色中依旧沉静锐利。
他的目光扫过院落,最后落在我身上,略一停顿,便走了过来。
“我回来了。”他开口,声音比记忆中更沙哑了些,许是路途劳顿。
“嗯。”我应了一声,一时间不知该说什么,只道:“一路辛苦。热水与饭食已备下,将军可要先洗漱?”
他点点头,没有多余寒暄,径直往正房走去。他的背影挺拔,步伐稳健,看不出半分疲态,只有久经沙场之人的利落。
晚膳时,我们相对而坐。桌上菜肴简单,远不如昔日侯府精致。他吃得很快,但举止并不粗鲁。席间只有碗筷轻碰之声,沉默得令人有些不适。
“北疆……一切可还顺利?”我终究先开了口,试图打破这僵局。无论如何,他如今是我名义上的夫君,表面的关切总是要的。
“尚可。”他简短答道,顿了顿,又补充,“边关已入冬,暂时无大战事。”
又是沉默。我想起清茗轩中李瑾的话,又想起柳如烟的讥讽,心中烦闷,便也失了继续攀谈的兴致。
数日后,宫中淑妃娘娘寿辰,举办宫宴。出乎意料,萧煜竟收到了请柬,而我,作为他的夫人,亦在受邀之列。
这是我自家中变故后,首次正式重返京城顶级的社交场合。我知道,无数双眼睛正等着看我这位“罪臣之女”、“低嫁武夫之妻”的笑话。
采薇为我选了套颜色较稳重的藕荷色织锦长裙,头面只用素银点翠,力求不出错,也不招摇。萧煜则换上了崭新的五品武官服,深青色的袍子衬得他身姿愈发笔挺,沉默地走在我身侧,却莫名让那些投射过来的打量目光收敛了几分。
踏入宫宴大殿,富丽堂皇与暗流涌动同时扑面而来。我能感觉到那些隐蔽的视线,好奇、怜悯、幸灾乐祸……如芒在背。我们按品级在偏后的位置落座。
果然,酒过三巡,柳如烟便与几位相熟的贵女袅娜而来。
“呦,这不是明珠妹妹吗?”柳如烟笑吟吟开口,声音恰到好处地让周围几桌听清,“这身衣裳倒是素雅,只是……妹妹从前最爱浮光锦的华彩,那才衬得起侯府千金的身份呢。如今真是……换了天地了。”她目光似有若无地扫过萧煜。
另一位鹅黄衣裙的贵女接口,声音娇脆:“如烟姐姐快别勾起明珠姐姐伤心事了。如今萧大人年轻有为,立了军功呢!只是武职升迁,到底辛苦些,不比文官清贵悠游,姐姐怕是要多操劳了。”话里的刺,清晰可辨。
我攥紧了袖中的帕子,指尖冰凉,胸口堵得发闷。这些昔日围着我奉承的人,如今争先恐后来踩上一脚。
我正欲开口,身侧响起一个低沉平静的声音:
“原来康宁伯世子夫人,对内子衣着如此挂怀。”
萧煜不知何时已放下酒杯,转过身,目光平平地看向柳如烟等人。他语气毫无波澜,却自有一股无形的压力,让那几个贵女的笑僵在脸上。
柳如烟脸上闪过一丝不自然,强笑道:“萧大人说笑了,我们姐妹只是叙旧。”
“叙旧?”萧煜眉梢几不可察地动了下,视线转向那鹅黄衣裙的贵女,“方才听闻姑娘议论武职清贵?不知姑娘府上哪位尊亲于国朝边防有建树?萧某愿闻其详。”
那贵女脸色瞬间白了。她父亲只是个从四品文官,兄长荫封闲职,何谈边防建树?
萧煜不再看她,目光落回柳如烟身上,依旧平淡:“内子性情如何,不劳外人置喙。萧某是粗人,只知功名但在马上取。边关将士戍守血战,护的是大周疆土,亦是京中安享的太平。至于清贵与否,”他嘴角极淡地勾了一下,带着边关风沙磨砺出的冷峭,“非深闺妇人可妄议。”
一席话,不疾不徐,不卑不亢,却字字如裹着棉布的针,扎得人生疼。直接将柳如烟等人的浅薄无礼剥露于人前。周围几桌顿时安静下来,不少目光带着讶异重新审视这位新任的游骑将军。
柳如烟几人脸色阵红阵白,尴尬得无以复加,勉强扯出个笑容,悻悻然告退了。
我怔怔地看着萧煜宽阔的肩背,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复杂情绪。震惊于他言辞的犀利,意外于他竟会出面维护,还有一丝……连自己都不愿深究的,细微的依赖感。他竟然就这样,用最直接的方式,挡在了那些恶意之前。
他转过身,见我望着他,神色依旧没什么变化,只低声道:“无关之人,无需费心。”
那一刻,在他沉静的目光笼罩下,我忽然觉得,这块“边关顽石”,似乎并非我所以为的那般简单冷硬。他像一口深潭,表面平静无波,内里却自有乾坤。
宫宴之后,萧煜在府中的时间似乎多了一些。他依旧沉默,大部分时辰待在书房,不知是处理公务还是看书。我们之间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,因那日的维护,横亘在彼此间的冰墙,仿佛裂开了一道细微的缝隙。
然而,一封没有落款的信笺,悄然送到了我的妆台抽屉里。纸上只有一行熟悉的字迹:“明日上午,老地方,瑾。”
是李瑾。他再次约我在清茗轩的“听雨阁”见面。
捏着那薄薄的信纸,我指尖微颤。理智在叫嚣:江明珠,你已嫁作人妇,私下会见外男,尤其是皇子,于礼不合,风险极大。可情感却如藤蔓缠绕:他是唯一还在为我家事奔走的人,是旧日情感的寄托,我迫切需要知道案情的进展,需要他亲口确认那个希望。
挣扎良久,对家族冤屈的关切,对过往的一丝不甘,终究压过了理智。我决定赴约。
出门前,我刻意换了身颜色稍鲜亮的衣裙,对镜整理了鬓发。刚出房门,便在廊下迎面遇上了从书房出来的萧煜。他穿着深青色常服,目光落在我身上,停留了一瞬。
“要出去?”他问,声音听不出情绪。
我心虚地垂下眼睫,低声道:“嗯,想去城南的绸缎庄看看……开春了,或许有些新样子。”
萧煜静默了片刻。那沉默并不长,却让我感觉像是被无形的网罩住,有些透不过气。他没有追问,只淡淡道:“早些回来。”
直到坐上马车,驶离萧府所在的街巷,我才缓缓舒出一口气,仿佛挣脱了某种束缚。但心底那点莫名的不安,却并未完全消散。
再次踏入“听雨阁”,李瑾已在等候。他今日穿着月白色常服,更显温润如玉。
“明珠。”他迎上来,眼中是毫不掩饰的关切,“你来了。脸色似乎比上次好些了。”
“殿下。”我福了福身,勉强扯出笑容。
寒暄几句,我便迫不及待切入正题:“殿下,我父兄的案子……”
李瑾的神色变得凝重,他示意我坐下,亲自为我斟了杯茶:“明珠,我知你心急。此事我一直在暗中查访,只是……阻力比想象中更大。”
“阻力?”我心头一紧,“可是有了眉目?”
“线索是有的,”李瑾压低声音,“指向都察院某位官员,可能与当年所谓‘证据’的呈递有关。但此人背景深厚,与朝中多位大员关系盘根错节,若无确凿铁证,轻易动他不得。”
他言辞恳切,眉头深锁,似乎确实遇到了难关。可我听在耳中,却觉得有些空泛。具体是哪位官员?有何背景?查到了什么线索?他一概未提。
“殿下,那……那我们该如何是好?难道就这样等下去吗?”我忍不住追问,语气带上了急切。
李瑾握住我的手,目光温柔而坚定:“明珠,你要信我。我比你更希望早日还江家清白。但此事急不得,需从长计议,步步为营。况且……”他顿了顿,眼中闪过一丝怜惜与为难,“你如今毕竟是萧煜之妻,我若动作太大,惹人注目,恐会招来非议,于你名声有损,反倒可能打草惊蛇。”
又是“从长计议”,又是“恐惹闲话”。与上次几乎如出一辙的措辞,让我心中那点期盼的热度,一点点冷却下去。他将进展缓慢的原因,隐隐归咎于我已嫁人的身份?还是说,这本身就是一种委婉的推脱?
一种夹杂着失望和疑虑的冰凉感,慢慢从心底升起。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意识到,李瑾的承诺,或许更多的是安抚,而非切实的行动计划。
就在此时,雅座外传来掌柜殷勤的招呼声和沉稳的脚步声,似乎有贵客临门。隐约听见“兵部”、“萧大人”、“述职”等零星字眼。
萧煜?他今日也来了清茗轩?还是巧合?
李瑾显然也听到了,他松开我的手,神色微凝,低声道:“明珠,此地不宜久留,你先回去。记住,耐心等待,切莫轻举妄动,一切有我安排。”
我心中乱成一团,点了点头,戴上帷帽,与采薇匆匆从另一侧楼梯离去。
回府的马车上,我靠在车壁,只觉得身心俱疲。李瑾那闪烁的言辞,与萧煜近日沉静却切实的存在,在我脑中反复交错。
刚踏入院门,便见萧煜负手立在正屋檐下,似乎在看着庭中那株尚未发芽的老树。听到脚步声,他转过身,目光沉静地落在我身上,依旧没有问我买了什么,看了什么花样。
他只是看了我片刻,然后缓缓开口,声音不高,却清晰地传入我耳中:
“京城看似繁华,实则暗流甚多。夫人如今是萧某的妻子,行事还须多加斟酌。有些旧路,看着熟悉,或许早已荆棘遍布,踏上去,恐会伤及自身。”
我心头猛地一撞,倏然抬头,对上他深邃无波的眼眸。他那句话,分明是意有所指!他知道了?他知道我去见了李瑾?
他没有戳破,也没有质问,只是用这样一种近乎直白却又留有余地的方式,点醒我。
这一刻,面对他洞悉一切却依旧平静的目光,再回想李瑾那温柔却空泛的承诺,一种荒谬而清晰的认知袭上心头:这个沉默寡言、被我视为生命意外闯入者的男人,或许比那个曾让我倾心信赖的皇子,更清醒,也更……可靠?
这个念头让我心惊,也让我愈发心乱如麻。我匆匆应了声“知道了”,几乎是逃也似的,快步走回了自己的房间。
窗外,不知何时聚起了乌云,天色阴沉下来,压得人透不过气。
自那日被萧煜点醒后,我心中对李瑾的疑虑如同春草,不受控制地滋生蔓延。我开始有意回避与“清茗轩”、“三皇子”相关的任何消息,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观察我这名义上的夫君,以及这座我暂时栖身的小院上。
萧煜似乎更忙了。兵部的差事显然不轻松,他有时在书房待到深夜,窗纸上映出他伏案的身影。我偶尔借口送些宵夜,总能瞥见书案上除了兵书舆图,还有一些涉及户部钱粮、工部器械的文书,甚至有几本厚厚的《大周律》。他并非我想象中只知冲锋陷阵的武夫。
一日,我无意听到前来拜访的兵部同僚在院中闲聊,言语间提及萧煜在武库清吏司的一次核算中,揪出了一笔陈年糊涂账,言辞犀利,条理清晰,连上官都暗自点头。那同僚离去时叹道:“萧兄真是心细如发,又能文能武,以前在边军,怕是埋没了。”
埋没?我站在廊柱后,心中微动。他似乎总在打破我的既定认知。
又过了些时日,或许是因为北疆之功和兵部差事办得妥当,萧煜被正式调入兵部武库清吏司,任员外郎,仍是从五品,却从纯粹的军职转为了更有实权的京官,意义截然不同。
府中往来的人渐渐多了些,虽远谈不上热闹,但也绝非昔日的门可罗雀。我发现萧煜待人接物自有章法,沉稳持重,不卑不亢,与那些浮躁的京官截然不同。
更让我意外的举动发生在一个傍晚。管家捧着府库的钥匙、对牌和一摞账本,恭敬地送到了我面前。
“爷吩咐了,日后府中一应开支用度、仆役调度,皆由夫人掌管。”管家垂首道。
我愣住了。自嫁入萧家,因心存去意,也因赌气,我从未过问府中事务,一切均由管家打理。萧煜此举是何意?试探?还是……某种意义上的认可?
“我……未曾独自管过家,只怕疏漏,辜负将军信任。”我有些迟疑。在侯府时,我看过母亲理事,学了些皮毛,但从未真正上手。萧府虽小,仆役关系、日常用度,想必也有其微妙处。
“夫人不必过虑。”萧煜的声音从身后传来。他不知何时已回来,站在门口,“管家会从旁协助。府中人事简单,正可让夫人熟悉。往后……”他顿了顿,目光落在我略显无措的脸上,语气平稳,“总要学着打理。”
他的目光沉静,没有催促,也没有期待,仿佛只是陈述一件理所当然的事。我看着他,忽然想起宫宴上他挡在我身前的背影,想起他那些隐晦却直接的提醒。
鬼使神差地,我接过了那串沉甸甸的黄铜钥匙。
掌家并非想象中容易。府中仆役虽不多,却各有心思。有见我年轻又是“罪臣之女”而暗暗轻视的,有欺我不懂行市想在采买上捞油水的,也有倚老卖老、办事拖拉的。
但我江明珠,岂是轻易认输的性子?我将侯府中学到的规矩拿了出来,先梳理账目,明确各项开支定例;再召集仆役,清晰分派职责,赏罚条例一并言明。起初有人阳奉阴违,我便抓一两个典型,或罚月钱,或调去做粗使,毫不容情。同时,对勤恳本分的,也不吝赏赐。不过半月,府中风气便为之一肃,诸事井井有条。
在这个过程中,我隐隐感觉到,萧煜并非完全撒手不管。偶尔我遇到棘手的事(比如有个婆子与外面铺子勾结虚报价格),管家总会“恰好”提点一两句,而事后想来,那些提点往往切中要害。萧煜并未直接插手,却在我看不见的地方,为我悄然扫除了一些障碍。
一日,我在核对近几个月的账本时,发现一笔支付给城南“翰墨斋”的款项。数额不大,但名目只含糊写着“文房用品”。翰墨斋我知道,并非城中知名的笔墨铺子,位置也有些偏僻。
我召来管家询问。管家眼神闪烁了一下,躬身道:“回夫人,这是爷吩咐的支出,具体用途,老奴也不甚清楚。”
心中起疑,我决定亲自去看看。换了身不起眼的衣裳,只带采薇一人,去了城南。
翰墨斋门面狭小陈旧,客人稀少。掌柜是个五十岁上下、眼神精明的瘦削男子。我以想买些上好松烟墨为由,与他攀谈。他起初有些戒备,直到我似无意间提起“萧府”、“账目”、“旧卷宗”等词,并观察他神色。
听到“旧卷宗”时,掌柜的眼神几不可察地缩了一下。他左右看了看,压低声音道:“夫人可是为萧爷询问那批‘旧档’誊抄的进度?请放心,关于北境军伍人员变动录的那部分,小店正在加紧核对笔迹与印鉴,还需些时日,定会仔细办好。”
北境军伍人员变动录?!
我的心猛地一沉,随即剧烈跳动起来。这不是普通的文房采买!萧煜在暗中调查与北境军务相关的东西?是……与我父亲当年的事有关吗?他为什么要私下做这些?是为了查明真相,还是……另有图谋?
巨大的震惊和纷乱的疑问瞬间攫住了我。我勉强维持镇定,又随意买了点墨锭,便匆匆离开了翰墨斋。
回到萧府,我站在庭院中,望着书房那扇紧闭的房门,第一次觉得,里面那个男人身上笼罩的迷雾,如此浓重。他不再仅仅是我被迫接受的“粗鄙武夫”,也不仅仅是名义上冷淡疏离的夫君。他像一把藏在朴素鞘中的剑,正在我毫无察觉的时候,悄然露出了一丝凛冽的寒光。
知晓萧煜可能在暗中调查与父兄旧案相关的线索后,我的心境再也无法保持表面的平静。一股难以言喻的期盼与恐惧交织缠绕——期盼他真的能找到翻案的铁证,恐惧这一切背后是更深的陷阱,让我从短暂的希望之巅再次跌落。
这种复杂心绪让我在面对萧煜时,不由自主地带上了更深的探究和一丝连自己都未察觉的依赖。然而,命运并未给我太多时间去消化和印证。
一场突如其来的宫宴,再次将我抛入了湍急的漩涡。这次是庆贺端亲王西南大捷的庆功宴。端亲王是瑞敏郡主的父亲,圣眷正隆。宴席之上,珍馐罗列,歌舞曼妙,一派喜气洋洋。皇帝显然心情极佳,酒过数巡,竟在众目睽睽之下,朗声宣布:
“皇三子瑾,品性端良,已至婚龄。端亲王嫡女瑞敏,娴雅聪慧,乃功臣之后。朕心甚悦,特赐婚二人,择吉日完婚,以成佳偶,慰功臣之心!”
“嗡——”
仿佛有洪钟在耳畔震响,我手中的象牙箸“叮”一声轻响,磕在碗沿。周围瞬间爆发出潮水般的恭贺之声,而我却像被骤然抽离了喧嚣,置身于冰冷的真空之中。四肢百骸的血液似乎都在倒流,凝结成冰。
李瑾……他要娶瑞敏郡主了?那昔日梅树下“非卿不娶”的耳语算什么?那一次次“等我”、“信我”的承诺又算什么?原来柳如烟并非空穴来风,原来他口中的“从长计议”、“恐惹闲话”,不过是早有预谋的敷衍和拖延!我所珍视的、赖以支撑的那点旧情与希望,在皇权与利益的联姻面前,薄脆得像一张一戳即破的糖纸。
巨大的荒谬感和灭顶的羞辱如同冰水混合物,将我浸透,冷得发颤,又堵得窒息。我死死掐住掌心,用尖锐的疼痛逼迫自己挺直脊背,维持脸上最后一点僵硬的表情,不让泪水溃堤。
就在我几乎要被这无声的崩塌吞噬时,桌下,一只温热而干燥的大手,悄然覆上了我紧握成拳、指甲深陷的手。那手掌宽厚,带着薄茧,温度透过我冰凉的皮肤,清晰传来。
我浑身一颤,侧过头,对上萧煜沉静的侧脸。他并未看我,依旧目视前方,仿佛只是随意地将手搁置。但那掌心传来的稳定热量,却像一道微弱却坚韧的绳索,将我从冰冷的深渊边缘,轻轻拉回了一丝。
他没有说话,没有安慰,甚至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,只是那样静静握着,任由我指尖的颤抖,逐渐平息在他掌心的沉稳里。
宴席的后半程,我如同提线木偶,不知身何处,魂何在。直到坐上回府的马车,车厢隔绝了外界的一切,我一直紧绷的弦骤然断裂,泪水终于无声地汹涌而出,沾湿了前襟。
萧煜坐在我对面,沉默地看着我,没有出言打扰,也没有递帕子。直到我哭得声噎气堵,渐渐只剩下低微的抽泣,他才将一方素净的棉帕放在我手边。
“为虚情假意伤神,徒耗心力。”他的声音在狭小的车厢内响起,低沉而平静,带着一种穿透迷雾的清醒。
我抬起泪眼朦胧的脸,看向他逆着窗外微弱光线的轮廓:“你……早就知道会如此,是不是?”
萧煜没有否认,淡淡道:“端亲王手握西南兵权,圣心正眷。三皇子需要强援。”
原来,他一直冷眼旁观着我的自欺欺人。一股夹杂着被看穿的难堪和残余不甘的恼意窜起:“那你为何不早说?!”
“早些说,你会信吗?”他反问,目光在昏暗光线中锐利如初,直直刺入我心底最虚弱的角落。
我哑口无言。是啊,在他沉默的行动与李瑾甜蜜的谎言之间,我始终选择相信后者编织的幻梦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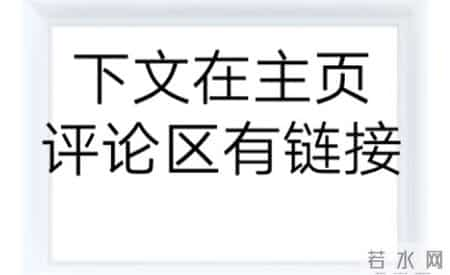
声明:本站所有文章资源内容,如无特殊说明或标注,均为采集网络资源。如若本站内容侵犯了原著者的合法权益,可联系本站删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