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间故事:穷秀才遇贵夫人,神笔马良画天下,金榜题名状元郎
明嘉靖三十七年,江南水乡,梅雨初歇。苏州府吴江县有个落魄秀才,名叫柳文修。此人年方二十有三,眉目清朗,颇有才气,无奈家道中落,父母双亡后,只余三间漏雨的祖屋和半架残书。柳文修白日里在城东“松鹤书院”做教书先生,晚上则借着一豆灯光苦读诗书,盼着来年秋闱能一举中第,光耀门楣。
这日黄昏,细雨又起。柳文修撑着把破油伞从书院出来,怀里揣着刚领的五百文束脩——这是他一个月的收入。路过城南“文宝斋”时,他不禁驻足。橱窗里新到了一批湖笔,其中一支紫毫笔,笔杆温润如玉,毫尖饱满,标价三两银子。
柳文修摸了摸怀里的铜钱,苦笑摇头。正欲离开,却听见身后传来女子惊呼。回头一看,一辆青绸马车陷在雨后泥泞中,车夫正费力鞭打马匹,车轮却越陷越深。马车帘幕掀起一角,露出半张脸来——那是一位年轻妇人,约莫二十五六岁年纪,云鬓轻挽,眉目如画,虽只匆匆一瞥,已见端庄气度。
柳文修不及多想,上前帮忙推车。他本就清瘦,使尽力气,泥水溅了一身,车轮才勉强转动。正要松口气,脚下青石板湿滑,他一个趔趄,竟摔倒在地,怀中铜钱撒了一地。
马车窗帷再次掀起,妇人轻声吩咐了句什么。一个丫鬟模样的少女下车,递来一方素帕:“先生请擦擦脸。我家夫人说,多谢先生相助,这些钱请先生收下。”丫鬟手中是个锦囊,沉甸甸的。
柳文修连忙摆手:“举手之劳,岂敢收酬。只是...”他看着满地铜钱,有些窘迫。
妇人此时亲自下车。她身着淡青色杭绸褙子,下系月白罗裙,发间只簪一支白玉簪,通身素净,却自有一股清华之气。她弯腰拾起几枚铜钱,轻轻放在柳文修手中:“先生高义,令人敬佩。这些本就是您的钱,请收好。”声音温婉,如春风拂柳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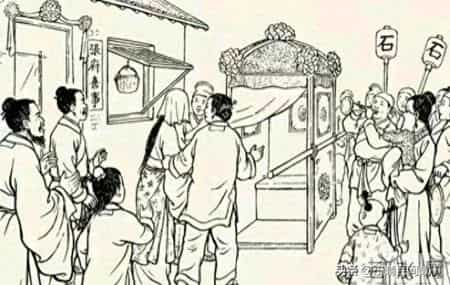
柳文修这才看清妇人容貌——眉似远山,目若秋水,只是面色略显苍白,眉宇间似有淡淡愁绪。他忽然觉得这面容有些熟悉,却想不起在何处见过。
“晚生柳文修,多谢夫人。”他躬身行礼。
妇人眸光微动:“可是住在城西柳树巷的柳秀才?”
“正是。夫人如何得知?”
妇人浅浅一笑,却不回答,只道:“素闻柳秀才才学出众,今日一见,果然品性高洁。”她看了看文宝斋的橱窗,“方才见秀才对着那支紫毫笔驻足良久,可是喜欢?”
柳文修脸上一热:“只是欣赏罢了。”
妇人微微颔首,转身对丫鬟低语几句。丫鬟走进文宝斋,不多时便拿着那支紫毫笔出来。妇人接过,亲自递给柳文修:“宝剑赠英雄,好笔赠才子。这支笔,便当是谢礼。”
柳文修大惊:“这如何使得!此笔贵重,晚生断不能收!”
“收下吧。”妇人将笔塞入他手中,指尖轻触,冰凉如玉,“若有朝一日金榜题名,莫忘今日便是。”说罢转身上车,帘幕垂下前,又深深看了他一眼。
马车缓缓驶离,柳文修握着那支温润的紫毫笔,愣在原地。笔杆上似乎还留着妇人指尖的凉意,鼻尖似有暗香萦绕。
回到家中,柳文修点亮油灯,仔细端详那支笔。紫毫光润,笔杆是上等的湘妃竹,竹节处天然生有几处淡褐斑纹,宛如泪痕。他将笔蘸了清水,在旧纸上随意一划——笔锋竟如游龙走蛇,出墨均匀饱满,真乃极品。
“这样的笔,岂是我这等寒士配用的?”柳文修喃喃自语,却终究舍不得,小心收在笔匣中。
当夜,柳文修做了个怪梦。梦中他手持紫毫笔,在一幅长卷上挥毫。画中山水灵动,花鸟欲飞,最奇的是,他画一轮明月,月便真的洒下清辉;画一树红梅,梅香竟透纸而出。正惊奇间,忽见那日所遇的妇人立在梅树下,对他盈盈一拜,化作一缕青烟消散。
柳文修惊醒,窗外月色如水。他鬼使神差地取出紫毫笔,铺开一张宣纸,凭着记忆画起那妇人的面容。说来也怪,他素来不善丹青,此夜下笔却如有神助,不多时,纸上已现出那妇人的眉眼。正要勾勒发髻时,笔尖一顿,一滴墨落在画中人的眼角,竟似一滴泪痕。
柳文修正懊恼,却见那墨迹渐渐晕开,画中人眼角微红,更添凄婉。他心中一颤,莫名感到一阵悲凉。
次日,柳文修向书院告假,去了城隍庙前的卦摊。摆摊的是个盲眼老道士,人称“张半仙”,据说卜卦极准。
柳文修递上三文钱:“请道长解一梦。”
他将梦境细细说了,却隐去了妇人和紫毫笔的细节。张半仙捻着胡须,沉吟良久:“秀才梦中能画物成真,这是得了‘神助’啊。只是...月有阴晴圆缺,梅开自有落时,此梦主大喜亦主大悲。老道多嘴问一句,秀才近日可曾得了什么不同寻常之物?”
柳文修心头一跳,含糊道:“不过是寻常笔墨。”
张半仙不再追问,只道:“物各有主,缘各有因。秀才若得了非凡之物,当知非凡之因果。切记:画虎画皮难画骨,知人知面不知心。”
这话说得云山雾罩,柳文修心中疑窦更深。离开卦摊,他特意绕到城南打听,才知那日所遇的妇人竟是城中巨富周家的少夫人,姓沈,名清漪。周家做丝绸生意,富甲一方,只是人丁不旺。三年前,周家独子周文远娶了沈清漪,谁知成婚不满一年,周文远便暴病身亡。沈清漪年纪轻轻守了寡,深居简出,极少露面。

“周少夫人啊,可是个苦命人。”卖胭脂的婆子叹道,“过门不到一年就守寡,周老夫人怪她克夫,对她颇为刻薄。这么些年,她就守着个‘贞节牌坊’过日子,连娘家都回得少。”
柳文修闻言,心中复杂。原来那日所见眉间愁绪,竟是这般缘故。
时光荏苒,转眼秋闱在即。柳文修日夜苦读,那支紫毫笔成了他最趁手的工具。说来也奇,用此笔作文,文思泉涌,下笔如飞,字字珠玑。书院夫子看了他近来的文章,都惊叹进步神速。
这夜,柳文修改完学生课业,已是三更。他铺纸练字,写着写着,不知不觉又画起了沈清漪的肖像。这些日子,他竟养成了这个习惯,画了不下十幅,幅幅生动,却总觉得缺了些什么。
正凝神间,忽听窗外有人轻叹。
柳文修一惊:“谁?”
推窗望去,月色下立着一人,淡青衣衫,正是沈清漪。她比上次更显清瘦,面色苍白如纸。
“夫人怎会在此?”柳文修又惊又疑。此处是城西贫民区,周家豪宅在城东,相隔甚远,且夜深人静,她一个寡居妇人如何孤身来此?
沈清漪凄然一笑:“妾身冒昧,有一事相求。”她递上一卷画轴,“听闻柳秀才擅画,可否为妾身补全此画?”
柳文修展开画轴,见是一幅未完成的《春江花月夜》。画工精湛,气象开阔,远山近水,楼阁舟楫,无不精妙,唯独江心小舟上,该有的人物只勾勒了轮廓,未画面目。
“此画乃先夫遗作。”沈清漪轻声道,“他临终前未能完成,这些年,妾身寻遍画师,却无人能补其神韵。那日见秀才笔意不凡,故来相求。”
柳文修细看画作,笔法老练,设色淡雅,确是佳作。他沉吟片刻:“晚生尽力一试。只是需要些时日。”
“多谢。”沈清漪深深一拜,转身欲走,却又停步,“还有一事...若有人问起此画,万不可说是妾身所托。”说罢匆匆离去,消失在夜色中。
柳文修心中疑团重重,却不及细想,全心投入补画。说来也怪,每当他用那紫毫笔在画上添补时,便觉心手相应,如有神助。七日之后,画作完成——江心小舟上,一对璧人相依赏月,男子温文,女子清丽,虽只背影,却情意宛然。
最后一笔落下,柳文修长舒一口气。倦极伏案而眠,恍惚间又入梦境。这次他见沈清漪立于江边,对他含泪而笑:“多谢先生成全。”言罢纵身跃入江中。柳文修大惊,伸手去拉,却捞了个空。
惊醒时,天已微明。那幅《春江花月夜》在晨光中熠熠生辉,江心小舟上,不知何时多了两行小楷:“愿为西南风,长逝入君怀。”

字迹娟秀,墨迹犹新,竟像是刚刚写就。
柳文修怔怔看着那两行诗,心中涌起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。他忽想起张半仙的话——“物各有主,缘各有因”。
秋闱之日渐近,柳文修闭门苦读。这日,书院来了位不速之客——周家的管家,一个精瘦的中年人,姓赵。
赵管家开门见山:“柳秀才,听说你得了支紫毫笔?”
柳文修心中一紧:“确有此事。”
“那是我家少夫人的心爱之物,不慎遗失。还请秀才归还,周家必有重谢。”赵管家目光锐利。
柳文修想起沈清漪赠笔时的神情,摇头道:“此笔是周夫人亲自所赠,并非遗失。”
赵管家脸色一沉:“胡说!我家少夫人深居简出,岂会随意赠笔给外人?定是你巧言哄骗!秀才,周家不是你能招惹的,识相的就交出来。”
柳文修性子外柔内刚,闻言反而镇定下来:“笔是周夫人所赠,若要收回,也当由她亲自来取。”
赵管家冷笑数声,拂袖而去。
当夜,柳文修家中遭了贼。门窗完好,唯独那支紫毫笔和《春江花月夜》的画轴不翼而飞。柳文修又气又急,却无可奈何。
次日一早,他正要报官,却见赵管家又来了,这次态度恭敬许多:“柳秀才,我家老夫人有请。”
周府深宅大院,气象森严。正厅上首坐着位满头珠翠的老夫人,正是周家主母周王氏。她年约六旬,面容严肃,目光如刀。
“柳文修?”周王氏上下打量他,“听说你有些才学。老身也不绕弯子——你与清漪,是何关系?”
柳文修躬身道:“晚生与尊府少夫人只有一面之缘,蒙赠笔之情,并无他故。”
“一面之缘?”周王氏冷笑,“那你为何为她补画?又为何收她私赠之物?你可知道,寡妇私授外人物品,是何等罪名?”
柳文修挺直脊背:“夫人赠笔,是酬谢晚生推车之劳;补画之事,是晚生感念周公子才情,自愿为之。光明磊落,并无私情。”
“好个光明磊落!”周王氏一拍桌子,“你可知那支笔的来历?那是文远的遗物!清漪那贱人,竟将亡夫遗物私赠外人,其心可诛!”
柳文修愕然。他忽然明白,为何沈清漪赠笔时说“若有朝一日金榜题名,莫忘今日”;为何她眉间总有化不开的愁绪。
“老夫人,”柳文修正色道,“少夫人赠笔时曾说,愿晚生有朝一日金榜题名。她是以此激励寒士,光耀斯文,此心可敬,何以见责?”
周王氏怒极反笑:“好,好一张利口!来人,请家法!老身今日就要问问那贱人,是何居心!”

正混乱间,忽听一声:“且慢。”
沈清漪缓步走入厅中。她一身素衣,不施脂粉,却自有一种凛然之气。她先向周王氏一礼,然后转向柳文修,目光复杂:“柳秀才,妾身连累你了。”
“清漪,你还有脸出来!”周王氏喝道,“私授亡夫遗物,你可知罪?”
沈清漪跪倒在地:“媳妇知罪。但那支笔,并非先夫遗物。”
“胡说!那湘妃竹紫毫笔,是文远生前最爱,老身岂会认错?”
沈清漪抬头,泪光盈盈:“母亲可还记得,三年前文远病重时,曾有人送来一支笔,说是能治他的病?”
周王氏一愣。
“那人说,此笔有灵,需有缘人持之,绘出心中所愿,便可成真。文远试了,画了健康之身,却毫无效用。”沈清漪凄然道,“他临终前将笔给我,说‘此笔非俗物,当赠与真才子’。这些年来,我见过多少所谓才子,无人能触动笔灵。直到那日见到柳秀才...”
她转向柳文修:“秀才可曾用此笔画过什么?”
柳文修猛然想起那些梦境,那些栩栩如生的画作,喃喃道:“我画过...画过夫人。”
厅中一片寂静。忽然,丫鬟惊呼:“画...画动了!”
众人顺着她的目光看去,只见厅中悬挂的一幅普通山水画,竟无风自动,画中溪水泛起涟漪,云气缓缓飘移。
沈清漪泪中带笑:“果然...此笔遇真主了。柳秀才,你梦中作画能成真,白日里却不知其能,是因为心意不纯。唯有至诚至真之心,才能激发笔灵。”
周王氏惊疑不定:“这...这是妖术!”
“非也。”门外传来苍老的声音。张半仙拄着竹杖,不知何时出现在厅外,“此笔乃前朝画圣遗物,名‘灵枢笔’。画圣临终前以心血淬炼,使其有灵。然宝物择主,非心地纯净、才华横溢者不能御之。周公子虽才,心中执念太深,故不能激发笔灵。柳秀才心怀坦荡,志存高远,正是此笔真主。”
他转向柳文修:“秀才,你可愿当众一试?”
柳文修心潮澎湃,点头应允。赵管家取回那支紫毫笔,柳文修接过,铺纸于案。他闭目凝神,想起这些年的寒窗苦读,想起父母的期望,想起沈清漪那句“金榜题名”,胸中激荡,挥毫而就——
画的不是山水花鸟,而是《寒窗读书图》。画中寒士夜读,孤灯如豆,窗外明月高悬。最后一笔落下,画中灯焰竟微微摇曳,月光洒落满纸清辉。
满堂哗然。
张半仙抚掌:“善哉!此笔得遇明主矣。”他对周王氏道,“老夫人,此笔留在周家,不过是一件玩物;赠与柳秀才,或可成就一段佳话。令郎遗愿,不正是如此么?”
周王氏默然良久,长叹一声:“罢了...文远在天有灵,也该欣慰。”她看向沈清漪,“这些年,委屈你了。”
沈清漪泪如雨下。
秋闱之日,柳文修携灵枢笔入场。三场文章,下笔如有神助。放榜之日,他高中解元。次年春闱,再传捷报,殿试之上,嘉靖皇帝亲阅其卷,见文章锦绣,字字珠玑,钦点为一甲第一名状元。
琼林宴上,新科状元柳文修紫袍玉带,风姿卓然。皇帝问其可有未了之愿,柳文修跪奏:“臣蒙天恩,不敢他求。唯有一事——苏州周氏遗孀沈氏,恪守妇道,敬老恤贫,且曾赠臣灵笔,激励苦读。请陛下旌表其节。”
皇帝准奏,御赐“贞孝流芳”匾额。
柳文修衣锦还乡那日,苏州城万人空巷。周府张灯结彩,迎状元公来访。席间,周王氏亲执柳文修手:“老身有一不情之请。清漪年轻守节,这些年为周家尽心尽力。如今陛下旌表,她贞名已全。老身想认她为义女,许她自由之身,将来...若遇良人,可再缔良缘。”
满座皆惊。沈清漪怔怔落泪,柳文修离席长揖:“老夫人仁德。”
又三年,柳文修任满回京,途经苏州,闻沈清漪在城郊办了义学,教贫家子女读书。他青衣简从前往探访,见学堂中,沈清漪素衣荆钗,正教孩童念诗。阳光透过窗棂,洒在她身上,宁静美好。

两人庭中相见,相视一笑。院中红梅初绽,暗香浮动。
“夫人可还作画?”柳文修问。
沈清漪微笑:“偶尔。只是不再画人物,只画山水花鸟。”
柳文修从袖中取出一卷画轴:“下官近日作了一幅《春江花月夜》,请夫人指点。”
画展开来,仍是当年那幅画的景致,只是江心小舟上,多了个执笔的书生,与赏月的女子并肩而立。远处,朝阳初升,江天一色。
沈清漪凝视良久,轻声道:“画得...极好。”
一阵春风吹过,画卷微动,画中江水似乎泛起涟漪,红梅飘落几瓣,正落在两人肩头。
后来,柳文修官至礼部侍郎,一生清廉,致力文教。他始终珍藏着那支灵枢笔,却不再用作画成真之事,只作寻常笔墨。有人说,真正的“神笔”,不在画物成真,而在以笔墨传道,以文章济世。
沈清漪的义学越办越大,成就无数寒门子弟。她终身未再嫁,却活得充实自在。每年红梅开时,她会收到一盒京城带来的糕点,附一纸短笺,上书:“江南无所有,聊赠一枝春。”
这段故事在吴地流传开来,人称“神笔良缘”。后人作诗叹曰:
紫毫灵笔认真才,寒士风尘遇玉钗。
画里春秋原有梦,人间离合总关情。
贞名已全酬初志,金榜高登报旧怀。
莫道丹青能化物,至诚方能动天心。
而那支灵枢笔,在柳文修晚年时,被他捐赠给苏州文庙,供奉于先贤堂中。据说每逢大比之年,笔身会隐隐生辉,似在激励后来学子。这大概就是“神笔”最好的归宿——不是私藏之宝,而是天下公器,永佑斯文。

当您看到这里的时候,说明您已经看完故事,麻烦您点个关注点个赞,举手之劳是对我最大的鼓励!本故事纯属虚构!谢谢观看!
文章图片来源于网络,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!谢谢
声明:本站所有文章资源内容,如无特殊说明或标注,均为采集网络资源。如若本站内容侵犯了原著者的合法权益,可联系本站删除。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