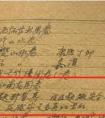民间故事:盐道白骨案
明朝时期,山东潍县出了件怪事。
那年腊月,北风刮得跟刀子似的,大清河的冰结得能跑马车。老盐商陈久龄家的三儿子陈墨书,失踪整整七天了。陈家上下急得团团转,报官、寻人、悬赏,能想的法子都想遍了,愣是没半点消息。
陈家在潍县是有头有脸的盐商,祖上三代贩盐,家底厚实。陈墨书生得白净,读过几年书,二十出头,刚接手家里部分盐务,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。这么个大活人说没就没了,搁谁都不信。
这日清晨,盐帮的一个老脚夫在城南乱坟岗附近拾柴火,忽然闻到一股怪味——咸腥里夹着腐臭。他拨开枯草丛,吓得一屁股坐地上:一具男尸仰面朝天,衣衫褴褛,左腿齐膝以下不翼而飞,伤口早冻得发黑。最骇人的是,尸身周围撒着一圈白花花的盐,在冬日惨淡的阳光下,闪着诡异的光。
衙门来人一瞧,正是失踪多日的陈墨书。
消息传到陈家,陈老爷子当场晕了过去。陈家老大陈砚池强撑着去认尸,只看了一眼,便背过身去干呕。老三那条断腿处,切口整齐得瘆人,不像野兽撕咬,倒像被什么利器一刀斩断。
仵作验尸后禀报知县刘文焕:陈墨书死于脖颈处的致命伤,凶器应是窄刃利器。断腿处虽有生活反应,说明是生前被砍,但并非死因。死亡时间约在五日前,也就是失踪后两日。
刘知县捋着山羊胡,眉头皱成个“川”字。命案本就棘手,偏又牵扯到盐商陈家。更怪的是现场那圈盐——私贩食盐在大明是重罪,这么明目张胆地用盐,是挑衅还是另有深意?
“查!先从陈家查起!”刘知县一拍惊堂木。
这一查不要紧,竟牵出陈家一桩陈年旧事。

陈老爷子陈久龄年轻时走南闯北贩盐,吃过不少苦。二十年前,他押一批盐从天津往山东运,在沧州地界遭了劫。劫匪凶悍,护盐的伙计死伤大半,陈久龄也被砍伤左腿,险些丧命。危急时刻,一个姓耿的镖师拼死相救,硬是杀出一条血路,保住了大半盐货,自己却中了毒箭,不治身亡。耿镖师临终前托付陈久龄照顾他怀有身孕的妻子。陈久龄满口答应,将耿家母子接到潍县,置了处小院安顿。
起初陈久龄还算尽心,每月送钱送物。可没过两年,盐务越做越大,应酬越来越多,去耿家的次数就少了。又过一年,耿妻染病去世,留下个三岁男娃,名叫耿三槐。陈久龄本想收养,可自家夫人不乐意,说自家三个儿子够闹腾了,哪还顾得上外人孩子?陈久龄便出钱将孩子托给一户远亲,起初还过问几句,后来渐渐淡了。
“那耿三槐后来怎样了?”刘知县问陈家老仆。
老仆叹气:“那孩子命苦,十二岁上得了场大病,左腿烂了,没钱医治,只得锯了。后来听说在码头上做些零活糊口,再后来...就不清楚了。”
独腿?
刘知县眼睛一亮:“他如今多大?”
“算来...该有二十二三了。”
与陈墨书年纪相仿,又是个独腿——刘知县立刻派人全城搜查独腿男子。不出半日,有衙役回报:城南破庙里住着个独腿乞丐,约莫二十出头,平日里在码头扛包,人称“耿瘸子”。但几天前,这人忽然不见了。
“搜他家!”
衙役们扑到耿三槐栖身的破屋,屋内空空如也,只在墙角找到个破包袱。打开一看,是几件打补丁的旧衣,还有一块褪了色的镖师腰牌,刻着个“耿”字。最可疑的是,包袱皮上沾着些白色晶粒,一尝,是盐。
“捉拿耿三槐!”刘知县下了海捕文书。
城里议论纷纷。有人说耿三槐是回来报仇的,嫌陈家忘恩负义;有人说他盯上陈家钱财,绑票不成下了杀手;更有人说,那圈盐是盐帮的标记,说不定牵扯私盐买卖...
陈家大少爷陈砚池这几日坐立不安。老三的丧事还没办利索,官差又频频上门,搅得家里鸡犬不宁。这晚,他翻来覆去睡不着,披衣起身,来到父亲书房。
烛光下,陈久龄老了许多,手里摩挲着一块旧玉佩——那是当年耿镖师留给他的信物。
“爹,耿家的事...”陈砚池欲言又止。
陈久龄长叹一声:“是我亏欠那孩子。可他...不至于下此毒手啊。”
“官府说人证物证都有,现场还撒了盐,明显是冲着咱家盐买卖来的。”陈砚池压低声音,“爹,您说会不会是...盐帮内部...”
话音未落,窗外“啪嗒”一声轻响,像是什么东西掉在地上。父子俩一惊,推窗去看,只见院墙根下黑影一闪而过。管家举灯笼来照,地上赫然是一小布袋盐,袋口散开,盐粒洒了一地。
袋子里还裹着张字条,歪歪扭扭写着:“盐债血偿。”
陈久龄捏着字条,手直哆嗦:“是他...真是他...”
案子似乎明了了:耿三槐怀恨在心,杀害陈墨书,还故意撒盐示威。刘知县加大搜捕力度,在各路口设卡,悬赏捉拿独腿凶犯。
但怪事又来了。
三日后,大清河下游的渔民捞起个麻袋,里面竟是条人腿,已经泡得发白。经辨认,正是陈墨书缺失的左腿。腿上也撒了盐,用粗麻绳捆得结实,绳结打法很特别,是水手常用的“渔人结”。
“这耿三槐在码头干活,会打渔人结不奇怪。”师爷分析。
刘知县却沉吟起来:“既然要弃尸,为何分两次?先抛尸乱坟岗,再扔腿入河,这不是多此一举?”
“许是慌乱所致?”
刘知县摇头,吩咐道:“去查查,最近码头、盐场可有什么异常;还有,耿三槐失踪前,跟什么人来往。”
这一查,又牵出另一条线。

潍县盐务,表面由几家大盐商把持,实则暗流汹涌。私盐贩子活动频繁,官盐常被掺假、克扣,盐价时高时低,百姓怨声载道。陈家在盐商里算规矩的,但树大招风,难免得罪人。
衙役从码头苦力口中得知,耿三槐虽然残疾,干活却拼命,为人仗义,常有工友接济他。失踪前几日,他曾跟一个外乡人喝酒,那人操天津口音,像是跑船的。
“天津口音...”刘知县想起陈久龄当年被劫,正是在天津到山东的路上。
与此同时,陈家内部也不太平。老三一死,盐买卖的担子全落在大哥陈砚池肩上。老二陈纸扇是个读书人,对生意没兴趣,整天吟诗作画。陈砚池忙得焦夜,这日查账,竟发现近来有几笔盐款对不上,缺口不小。追问账房,支支吾吾说是三少爷生前经手的,具体去向不明。
“老三糊涂!”陈砚池又气又急,却也无处查证。
夜深人静,陈砚池独自在账房对账,忽听门外有轻微响动。他警惕地喝问:“谁?”
没有回应。
他提灯开门,走廊空空。正要转身,脚下踢到个东西——又是一个小盐袋,比上次更小,里面没有字条,只裹着一枚铜钱,嘉靖通宝,边缘磨得发亮。
陈砚池认得这铜钱。小时候,耿三槐还没被送走时,常来陈家玩。有次陈砚池得了串糖葫芦,分给耿三槐一颗,那孩子舍不得吃,掏出一枚磨亮的嘉靖通宝,说这是他爹留下的,送给他当谢礼。陈砚池没收,那孩子失落了好久。
“难道真是他?”陈砚池心里五味杂陈。
次日,更惊人的消息传来:有人在城西土地庙看见耿三槐了!不是活人,是尸体——耿三槐吊死在庙梁上,也是独腿,身边散落着些盐粒。
刘知县带人火速赶到。死者确是独腿男子,二十出头,面容消瘦,脖颈有勒痕,是自缢身亡。死亡时间约在两日前。身上衣物与破屋里的相符,怀里还揣着那枚嘉靖通宝。
“结案了?”师爷小声问。
刘知县蹲下身,仔细查看尸体左腿断口。忽然,他眉头一皱:“这伤...不对。”
“怎么不对?”
“陈墨书的腿,切口整齐,是利刃一刀断骨。可这人的腿...”刘知县指着断肢处,“切口参差,像是多次切割所致,而且伤疤陈旧,至少十年以上。”
仵作细验后证实:耿三槐的腿伤确是旧伤,与陈墨书的新鲜切口完全不同。
“那这具尸体是谁?”师爷糊涂了。
刘知县不答,却问:“发现尸体的是谁?”
是个更夫,说昨晚巡夜时见庙里有光,今早好奇去看,就发现了。
“昨晚有光...尸体却已死两日以上。”刘知县冷笑,“有人故意把尸体摆在这儿,等我们发现。”
“可这人确实是耿三槐啊,年龄、残疾都符合...”
“残疾可以伪装,年龄可以相近。”刘知县站起身,目光锐利,“但伤疤伪造不了。这死者,恐怕才是真正的耿三槐——他早就死了,被人杀害后伪装成自杀。”
师爷倒吸一口凉气:“那杀陈墨书的...”
“另有其人。而且此人知道耿家旧事,故意用盐和独腿混淆视听,让我们以为耿三槐是凶手,再杀耿三槐灭口,做成自杀假象,一石二鸟。”
“可动机呢?仇杀?财杀?”
刘知县望向远处陈家高耸的盐仓,缓缓道:“恐怕,还是为了盐。”
他重新梳理线索:陈墨书经手的盐款有问题;现场两次出现盐;天津口音的外乡人;二十年前的劫案;伪造的独腿凶手...
“查!重点查陈家近年盐务往来,特别是与天津方面的交易;还有,找那个天津口音的外乡人!”
衙役四出,三日无果。就在刘知县焦头烂额时,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出现了——陈家老二陈纸扇主动来到县衙,说有话要讲。
陈纸扇平日不问家事,只爱书画。他拿出一卷画,展开是一幅《盐运图》,描绘盐船运盐的场景。画工精细,连船夫样貌都栩栩如生。
“大人请看这里。”陈纸扇指向画中一个船夫。
那船夫侧脸,额角有道疤,正在卸盐袋。

“这人我见过几次,跟老三来往。有次我去码头采风,见老三与他密谈,神色慌张。后来打听,这人叫孙疤脸,天津来的,常在河道跑船。”
“为何不早说?”
陈纸扇苦笑:“我本以为老三做些私下买卖,无伤大雅。直到他出事,我才想起这茬。这几日我暗中打听,孙疤脸在老三死后就离了潍县,但有人说在青州一带见过他。”
刘知县立刻派人赶往青州。同时,他对陈墨书经手的盐账进行彻查,发现缺口足有三千两白银,对应短缺的官盐约五百引(一引约200斤)。这么大数目,绝不是小打小闹。
五日后,孙疤脸在青州码头被抓。押回潍县,经不住拷问,全招了。
原来,陈墨书年轻气盛,不满父兄保守的经营方式,暗中勾结天津私盐贩子,用官盐文书夹带私盐,牟取暴利。孙疤脸就是中间人。合作半年,陈墨书却想撇开他们单干,私吞了最近一批货款。私盐贩子头目大怒,派孙疤脸来“清理门户”。
“杀陈墨书的不是你?”刘知县问。
“不是!我去找他理论,可去晚了一步,他已经死了!”孙疤脸喊冤,“我到时,他倒在血泊里,腿被人砍了,周围撒着盐。我吓坏了,赶紧跑。后来听说官府在找独腿的,我就想起耿三槐...”
“你怎么知道耿三槐?”
“陈墨书以前提过,说家里有个忘恩负义的独腿穷亲戚,还拿他当笑话说。我一想,正好嫁祸给他。我本来就在码头混,认识耿三槐,知道他独腿,跟陈家有旧怨。那天我骗他喝酒,套出他住处,半夜去杀了他,砍下他一条好腿,想凑成一对...”
“什么?”刘知县一愣,“你砍了耿三槐的腿?”
“是...我想着,既然陈墨书少条腿,就把耿三槐的腿砍下来,扔到别处,制造混乱。可砍下来才发现,那腿瘦得很,跟陈墨书的对不上...我就只扔了陈墨书的腿,耿三槐的腿...埋了。”
“那耿三槐的尸体呢?”
“我本想处理,可来不及了,就把他吊在土地庙,做成自杀。他本来就穷困潦倒,自杀也说得通。”
案情至此,似乎明朗:私盐纠纷引发凶案,孙疤脸杀人嫁祸。但刘知县总觉得哪里不对——孙疤脸到现场时,陈墨书已死,腿已被砍。那第一个凶手是谁?为何砍腿?为何撒盐?
他再次提审孙疤脸:“你说现场有盐?”
“有!白花花一圈,围着尸体。”
“盐袋呢?”
“没看见袋子,就地上撒着。”
刘知县猛然想起:两次出现的小盐袋,字条,嘉靖通宝...这些孙疤脸都不知道。也就是说,还有第三个人在暗中活动,用盐袋传递信息。
这个人,很可能才是真凶。
刘知县将目标重新锁定陈家内部。谁能轻易拿到盐?谁知道耿家旧事?谁熟悉陈墨书的行踪?谁能进入陈府放盐袋?

他秘密传唤陈府所有仆役,逐个询问。一个烧火丫头怯生生说,案发前几天,她看见大少爷陈砚池的贴身小厮福顺,深夜从盐仓出来,怀里鼓鼓囊囊的。
“带福顺!”
福顺被带来时,面如死灰,不等用刑就招了:是大少爷让他偷盐的。
“大少爷要盐做什么?”
“他说...说要祭祖,要上好的精盐。可后来,我在大少爷书房外偷听,他好像跟人吵架,说什么‘盐债血偿’...”
陈砚池被传到堂。面对质问,他起初抵赖,直到刘知县拿出那枚嘉靖通宝。
“这铜钱,你认得吧?耿三槐至死都带在身上。可它却出现在你账房外。不是你放的,就是真凶放的——他在提醒你,耿家的债,该还了。”
陈砚池瘫坐在地,终于吐露实情。
原来,陈墨书私贩盐的事,陈砚池早就察觉。他劝过几次,老三不听,反而变本加厉。案发那晚,陈墨书又偷运私盐,陈砚池追到城外理论,兄弟俩激烈争吵。陈墨书失口说出,二十年前陈久龄被劫,根本不是意外,而是陈久龄自己勾结匪类,演的一出苦肉计,目的是吞掉合伙人的本金,并借机摆脱耿镖师这个知情人。
“耿镖师发现了爹的秘密,爹就...就在他中箭后,故意拖延救治...”陈砚池声音发抖,“老三说,爹这些年做盐生意,黑白两道通吃,背地里不知害了多少人。他说我也干净不了,要是敢告发他,他就把这些全抖出来。”
陈砚池又惊又怒,推搡间,陈墨书摔倒,后脑撞上石头,当场毙命。
“我吓傻了...本想报官,可想到家丑,想到爹的名声...”陈砚池痛哭,“这时,暗处走出一个人...是个独腿男人。”
“耿三槐?”
“不,是个中年人,戴斗笠,看不清脸。他说他都看见了,可以帮我。他掏出刀,砍下老三一条腿,又撒了盐,说这样官府就会以为是盐帮仇杀或耿家复仇。他还要走了老三怀里的银票和盐引凭证。我六神无主,只能听他的...”
“后来呢?”
“后来,他让我偷些盐,说有用。再后来,官府查到耿三槐,他又让我在府里放盐袋、扔铜钱,制造耿三槐还活着的假象。他说,只有这样,才能彻底摆脱嫌疑。”
刘知县追问那独腿男人的细节。陈砚池只记得,那人左手缺一根小指,说话带点天津口音。
天津口音,缺指,独腿...刘知县猛然想起二十年前劫案的一个细节:当时匪首被耿镖师砍掉左手小指,仓皇逃走。
“你爹当年被劫,匪首是不是天津人?是不是缺一指?”
陈砚池茫然点头。
谜底揭晓:当年的匪首并未远遁,而是潜伏下来。他知晓陈久龄所有秘密,暗中监视陈家。陈墨书私贩盐,他或许也参与其中。那晚他尾随陈家兄弟,目睹命案,便趁机出手,既灭口(陈墨书知道太多),又控制陈砚池,还能继续操纵陈家盐务。
“他在哪?”
陈砚池摇头:“每次都是他找我,在城隍庙后墙缝留信。”
刘知县立刻布控。当夜,一个独腿黑影果然出现在城隍庙。埋伏的衙役一拥而上,那人功夫了得,打倒两人,翻墙欲逃,被刘知县一箭射中右腿,终于就擒。
摘下斗笠,是个四十多岁的汉子,左腿是木假肢,左手缺小指。他供认自己就是当年匪首,真名吴四。二十年来,他改头换面,暗中经营私盐网络。陈家是他的重要棋子,陈久龄的把柄一直捏在他手里。陈墨书想摆脱控制,他就借陈砚池之手除掉,再嫁祸耿三槐,一箭双雕。
“耿三槐呢?你杀了他?”
吴四冷笑:“那小子?我本想利用他残疾,扮凶手。可去找他时,发现他病得快死了。也好,省我动手。我给他个痛快,用他的尸首做文章。”
“你为什么总用盐?”
吴四阴森森道:“盐是什么?是钱,是命,是债。陈久龄靠盐发家,也因盐造孽。我让他子孙都死在盐上,让盐成了索命符,这才是真正的‘盐债血偿’。”
案件告破,吴四、孙疤脸斩立决;陈砚池误杀胞弟,又协同掩盖,流放三千里;陈久龄旧案被翻出,革去盐商资格,家产充公。曾经显赫的陈家,一夜崩塌。
行刑那日,潍县百姓围观看热闹。刘知县当众焚烧了查获的私盐,火光冲天,盐粒噼啪作响,像无数冤魂在哭泣。
后来有人说,每逢阴雨夜,乱坟岗附近总有咸腥味飘来,隐约还能看见独腿人影蹒跚而行。而陈家老宅,再无人敢住,慢慢荒废了。
只有城里的老人喝茶闲聊时,还会提起这桩“盐道白骨案”,末了总要叹一句:
“这人呐,做什么都不能亏良心。盐是白的,可心要是黑了,再多的盐也腌不回来。”

至于那枚嘉靖通宝,后来不知所踪。有人说被陈久龄带进了棺材,有人说被乞丐捡去换了馒头,也有人说,它还在潍县某个角落,静静等着下一个拾起它的人,继续那段关于盐、债务与人性的轮回。
声明:本站所有文章资源内容,如无特殊说明或标注,均为采集网络资源。如若本站内容侵犯了原著者的合法权益,可联系本站删除。